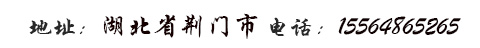霜降时节把酒话桑麻,是步入中年后温和
|
文 李志胜霜降近岁尾:“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白居易《岁晚》)这个时候,千里沃野,一片银色冰晶熠熠闪光,树叶枯黄,天气趋寒,初霜向冬。元·吴澄撰《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岁尾多旧事。从气象学上,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叫“早霜”或“初霜”,春季出现的最后一次霜称“晚霜”或“终霜”;但从人的心理预期上恰好相反,人们一般把春天作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起始季,而把暮秋看成是“精气不济”“廉颇老矣”的隐喻词。故此节气的表征多含颓废、肃杀之意。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意味着冬天即将开始。南宋诗人吕本中在《南歌子·旅思》中写道:“驿内侵斜月,溪桥度晚霜。”陆游于诗歌《霜月》中吟咏:“枯草霜花白,寒窗月影新。”霜降时节的这“一白”“一新”,在笔者看来,正是预告人生四季、各类旧事“粉墨登场”的急促锣鼓音。我的脑海里,首先有“摘棉花”的场景浮现:凉爽的秋风中,人人腰间系一个大布兜,一伸手,就将一朵软绵绵的“白云”采撷下来,塞进布兜,而后再摘、再塞,直到胸前鼓囊囊的,像个腆肚的孕妇,便折回地头,将那布兜的棉花转移到大布袋里……摘棉花看似轻松,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儿”,那对弯腰幅度的掌握,从裂开棉桃内采摘棉花的力道,全神贯注的眼神,都不能“掺一丝儿杂面”。去年初冬,我在郊外空地上发现了一棵棵未经完全采摘的“花柴”(棉花棵的俗称)。只见那雪白的棉絮,宛若一团团浓缩的白云溢出,映衬得四周的枯枝败叶,萧条、衰惫、无趣。同事老Z掏出手机,欲把“乡音未改”的棉花定格于镜头,我则下意识地摸摸身上的羽绒服,一边思量棉花的今生前世,一边暗暗测算羽绒与棉花这对“御寒兄弟”,从动物到植物、从品质到价值的转换距离。其二是“拾柴禾”。霜降杀百草。严霜打过的植物,生机全无,这时候捡回家的树枝、落叶、秸秆等非常干,极易燃火做饭。加之民间有谚语“满地秸秆拔个尽,来年少生虫和病”,所以秋冬之际拎筢拾柴禾,成为我们当年与春夏季割猪草一样重要的“课外活动”。同乡诗人、画家冯杰把小时候拾柴禾形容为“搂草打兔子”,他的随笔小品中这样回忆:“一天能拾到多少柴禾,取决于一架筢子质量的好坏。如能否打胜仗全靠武器的优劣。猪八戒有一副好筢子,还是铁筢,舞起来呼呼生风,西天取经才一路壮胆。乡村的筢子前部分筢齿是竹质的,后面的把柄是木质的,整体以结实轻盈为好,有的孩子则喜欢沉实粗大的筢柄,打架时能利用上。”冯杰先生的“冯氏幽默”,如同一架筢齿在上、筢把在下、紧贴青墙、风吹不动的“筢子”,在乡村农事的传承里,搂干草,搂豆叶,搂麦秸,搂花生叶,兼捎带打“诗意的兔子”……其三是观枫叶、赏菊花。人称“小杜”的唐代诗人杜牧和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分别用诗歌为这两项“娱乐活动”做了诠释:“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至今为枫叶爱好者所津津乐道;“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苏轼《和陈述古拒霜花》),则借暮秋的“菊花霜”,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喜爱和推崇。河南开封市自年以来,每年10月举办一届菊花花会,同时命名菊花为市花,既展示了开封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又演绎了经贸、旅游的联袂“大戏”,影响和意义深远。其四是“吃柿子”。柿子之甘美,有北宋词人张仲殊的诗:“味过华林芳蒂,色兼阳井沈朱,轻匀绛蜡裹团酥,不比人间甘露”为证。柿子之缘广,有民间“走亲戚拿柿饼当礼物”“用放软的柿子治冻伤”“霜降吃丁柿,不会流鼻涕”等习俗“搭台”。及至城市商场、超市热销的牛心柿、莲花柿、罗田甜柿和柿子汁、柿子酱、柿子酒等,无不于无形之中充当了“事事如意”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时逢秋暮露成霜,几份凝结几份阳。荷败千池萧瑟岸,棉白万顷采收忙。”诗人左河水的《霜降》诗,使人引发联想的旧事何止上边的“一二三四”。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果说早年的纺花车、织布机,是孩提时代温暖的记忆,那么现今的新衣裳、暄被褥,则是长大后温馨的依恋。霜降时节诸如棉花地、“花柴”棵等旧事,无不是我们步入中年后温和的眺望与怀想。可惜平原地带种棉花的越来越少,那像素洁棉花一样质朴的朋友也渐走渐失,我们偶尔从图片、资料里“把酒话桑麻”,用目光慰藉目光,用心灵问询心灵,进而以生活的点点滴滴,袅袅入耳、袭心,遂也有许多感喟,如棉絮溢出棉荚,如眺望中的春暖花开。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ongbailaa.com/cblxgls/11653.html
- 上一篇文章: 飞机医生守护河口区万亩林区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