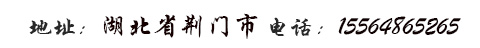美文殿堂西窗剪烛夜游宫
|
文 —— 西窗剪烛 文/夜游宫 (图片源自网络) 她右边面孔上一个淡淡青色的印记还在,但她贴着地面的另半边身子,已经融化了,桃红色半透明的东西在地上慢慢流淌开。 西凝山上原本有许多制蜡作坊,明初时还有作坊专门制作贡蜡送往京城为天子所用,名噪一时。不知什么时候起,渐渐有这样的传闻,说西凝山高超的蜡匠有一门特殊手艺,能制一种奇特的蜡,融合在人的肢体上,修补残肢断臂。更有人说,西凝山顶级的蜡匠会用蜡制出真的人,跑跳行走与一般人无二。 这些不知真假的传闻喧嚣一阵,复悄无声息在时光里沉睡,某一日经冷风一吹,又苏醒过来。 这时是个深冬,滴水成冰的天气,连家祖宅花园里但凡有枝叶的都凋落了,剩下满园光秃秃的大小枝桠,清寂寥落。秀庆跟在领路的丫鬟身后从花园里穿过去。狭窄的小径上铺了五彩的石子,硌在少女薄薄的鞋底,又硬又凉。她想开口叫小丫鬟走慢些,但“唉”了两声后发觉她离得更远了,像是躲避不及。 秀庆无计可施,默默跟在后头。她头一回来这庞大阴森的宅子,来给姐姐秀馨的新坟前添一炷香。 小丫鬟冬喜边走边拿眼角偷偷窥着跟在后面的人。 这女孩儿看似比自己大一两岁,眉眼生得很好。鼻梁挺直,眼窝也比一般人深一些,尖尖的面孔线条柔和利落,小巧的樱桃嘴儿被冻得乌青。最是那一双杏眼,水波清冽,多看一眼都能把人深深地溺进去。与她死去的姐姐,有七分相似。 前一刻,冬喜还含着五芳斋的酥皮糖,听连宅一帮子的小丫鬟们围着炭火盆,压低声调说那位新亡的少夫人。 她嫁来时所有人都惊艳了的。他们的表小姐淑莲本来也是美的,但在她面前就似一粒蒙了尘的棋子。她娇柔,精致,漆黑的大眼里似有一层终年不散的雾气,潋滟着迷蒙水光。美得灵气逼人——少爷肯大费周章从西凝山娶回来的美人,怎么会有差的。 新婚不久,老太太就给少爷连城君一单大买卖,叫他去北京。连城君放不下露珠似的娇妻,辗转流连了几天。老太太一怒之下提了拐杖去新房里打人,连城君最是怕奶奶,这才勉强去了。有人见到晨起请安时,老太太拿镶了铜皮的拐杖戳少夫人额头:“你男人在你床上不肯起来,你是得意了,连家上下百十口都等着喝西北风。什么不肯学,就学那些狐狸精,抓住男人不放手,离了男人不能活!” 十八岁的女孩孤立无援,跪在地上一言不发,一张绝美的尖尖面孔纸一样白,越发衬得眼仁漆黑,有胆小的丫鬟看了止不住地哆嗦:新主子眼里一丝生气也没有,竟不像是人。 少爷走后的两个月,祖宅接连起走了三次水,烧死了几个杂工,十来间下人屋子也烧得七七八八。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渐渐的,不知从哪里传开来的消息,到了这宅子每个人的耳朵里:少夫人原来根本不是人,是从西凝山来的蜡女。 西凝山的蜡人,与湘西的赶尸,苗疆的巫蛊一样,人人都似知道,但没人说的清。 西凝山的蜡匠会用融了血的蜡汁修补人的肢体残缺,更有厉害的人,会使一些不能见光的邪术,用蜡做出一个真正的,能走会跳的活人出来。 这么一看,少奶奶秀馨越发浑身疑点。 自少爷走后,开始还能听到她在园子里跟小丫鬟们说说笑笑,被老太太呵斥不分尊卑不成体统,房里的丫鬟婆子一并被罚,每人砸断一根小拇指。这下算是剪子绞布帛,干净利落,那方小小的园子里再没有一丝声响传出来了。有时路过的婆子见少夫人蜷在腊梅树下的躺椅上,似睡着了,瘦瘦小小一个人堆进臃肿繁复的锦绣华裳里,花枝上凝的露水“滴答”落在她不见一丝血色的面孔上,她的睫毛颤一颤,却动也不动,像足了西洋偶人。 少夫人再不与人说话,成天只要买蜡,一箱一箱的红蜡白蜡金漆蜡搬进去,她点了满满一屋子,不过几天就燃光了。再买。 直至三个月前一个大风的秋夜,不知蜡烛引燃了她房里的什么,整间园子,连同少奶奶一起,被烧得只剩下一堆冷灰。 连家的老太太端坐在梨花木的扶手椅子上。椅子下垫了厚厚的貂绒,油光水滑的毛皮从深褐色的扶手下滑出来一些,表小姐淑莲站在下首看见了,笑脸盈盈掖回去:“姑奶奶当心着凉。” “还是你知道心疼姑奶奶,没白疼你。”老太太双手搂着暖炉拢在广袖里,崭新的天青色绸缎袄子里是最细密的鸭绒,铺在熏笼上熏了好些天,从每一根绒毛深处腻出浓郁香味,在隆冬密封严实的房里,几乎要将人熏晕过去了。 是以冬喜轻手轻脚推开厅门,那股冷风卷进来时,所有婆子丫鬟都舒了口气,像又活过来了一遭。 冬喜小心翼翼地禀报:“老太太,我把秀庆带您跟前来了。” 垂老的妇人这时才微微掀开眼帘。她的眼角是向上吊的,似一只皮毛失去光泽的老狐狸,眼珠子却是黄褐色,在干涸的眼眶里慢慢慢慢地转动。她年轻时有一副十分妖娆的皮囊,那时连家的老爷已经娶了正妻,被她迷地神魂颠倒,从戏班子里娶了她回来做妾。前清崩倒时到处是叛军,连家举家躲避,这一路是他们的劫。老爷老太太,嫡出的长子长媳在路上都中流弹死了。再回来,就只剩下她与长房的七岁孙少爷连城君,孩子那么小能当什么事,这个漂泊无根的戏子就顺理成章成了连家的老太太、老祖宗。 她不说赐座,秀庆就这么一直站着。寒气从冰冷的地砖上侵上来,青灰色的单薄裤管在轻轻打颤。 “冷吧。”老太太倒笑起来,“这太湖边,比你们那个西凝山冷多了吧?” 秀庆只知点头。 冬喜吓得哆嗦,扯她衣角,“回答老太太问话,要说‘回老太太话’。” 老太太拢了暖炉,指甲上三寸长的玳瑁镶红玉甲套敲在铜炉上,“叮叮叮”一声声响得急促。“算了,现如今也比不得前朝了,小户人家越来越不讲究,这些礼数早就没了。” 秀庆不知说什么,修长的手指死命绞着短袄前襟上一粒盘扣。 老太太突然又转回话头来,“是冷吧。你姐姐被烧地尸骨无存,焉知不是怕冷惹出的祸?她是长房嫡孙的嫡妻,绫罗织锦的衣裳满满三大箱子,床榻上轻纱的幔子挂了一层又一层,她不但点一屋子烛火,又惧冷,时时要燃着炭。只一星半点的火气,就全着了。这么引火的物件儿摆了一屋子,海龙王在也是扑不灭的。当初我也跟城君说,这里冷,比不得西凝山,一方水土一方人,在自家地面上娶个体体面面的媳妇哪里不好了,扯这么远,大费周章把她从西凝山接过来,玉粒金莼好生供养着,还出了这种事。” 隔了很久,秀庆才听明白连家老太太是在说姐姐秀馨小户人出身不体面。 她咬着唇,眼泪氤氲着,但也只是含在眼眶没有落下来,连一丝丝的不满都不敢表露——这里青瓦灰墙的宅院一进连一进,夹墙的巷道一条接一条,来来往往的下人络绎不绝,但还是显得大,太大,太冷,似一座死寂的坟墓。秀庆觉得,只要一个疏忽,就会被吞噬进去,连骨头渣子也不剩下了。 底下的丫鬟婆子暗暗摇头。早知道少奶奶娘家没人,但也不想这么不济,死了都快两个月,才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娃娃,还似有点痴。只可惜了少夫人,那么一个美到极致的人儿,似一片花瓣凋落到水里,声响全无,只微微一点涟漪过后,什么都不剩了。 老太太岂有看不出的。 孙媳妇的死敷衍地滴水不漏,她原本也没怕过,只是对手相差太多,叫她也没了兴致,挥一挥手,“我乏了,都散了。” 冬喜带着秀庆,与一众丫鬟婆子都下去了。 表小姐淑莲一排银牙把嘴咬得煞白,老太太瞥她一眼,“行了,这小鱼小虾翻得起什么浪。还有十来天城君就回来了,你好好跟他相处,转了年你们成婚,过一阵有了孩子,管她死了的人再怎么美,也是黑土里的一捧灰,转眼也就忘了。” 淑莲面孔煞白,“姑奶奶,侄孙女还是有点……怕。” “怕,这时候知道怕了?当初我怎么说的,叫你跟城君一道去西凝山,你嫌路远,车颠,不肯去,叫他带了个妖精似的女蜡匠回来!”老太太一顿拐杖,怒其不争,“这回人都烧死了,还说什么怕。你只管去部署你的,再叫他们放出些风,把蜡女的事再编的神似一些。到时候城君即便回来,也只是个妖女引火烧死了自己。闹不出什么。别再缩手缩脚,等他翅膀再硬些,把我们老的少的扫地出门无依无靠,你再怕也来得及。” 淑莲打了个寒颤,一声“是”答应地瑟瑟缩缩。 老太太恨不能一杖敲醒她。在这些古老封闭的陈旧老宅里,每块青砖上都溅着那些个柔弱女子滚烫淋漓的鲜血,每方黑土下都掩埋着她们纤细无力的骨殖,每片花影下都有她们冤屈幽怨的游魂。生在这里,就是要斗争的。等着掩埋别人,或被别人掩埋。这是女人的战场,一刻也心软不得。 “心里不安的话,多去给她烧几回纸,叫她好上路。” 第二天清早就有丫鬟来请秀庆梳洗,早饭过后去祭拜少夫人秀馨。 老太太年事已高,深冬酷寒时不方便外出,表小姐淑莲陪着秀庆,与十来个提了元宝蜡烛的婆子丫鬟朝山上连氏祖陵走。隆冬时满山萧瑟,冷风刮在面孔上,砂纸摩擦似地疼。 “冷不冷?”淑莲问。 “嗯。”秀庆老老实实点头。 淑莲迟疑一会,“老太太说,这里恐怕太冷叫你受不住,待今天你祭拜完表嫂,明天休息一天,趁着天上有些太阳,就差人送你回去西凝山了。” 这番话说得已经不算婉转,秀庆当然听明白了,他们想她早早就回去。她有些舍不得,姐姐一个人在这里,这么一想,眼底立刻有了泪,唯恐自己哭出来,只模糊“嗯”一声。 淑莲是混在大宅子里的人,心眼毕竟比她多几个,瞥一眼就知道她在想什么,忍一会,说,“表哥对表嫂很好。” 就是对她太好了。若是差一些,老太太恐怕还安排了她去给他做平妻,就是太好,恐怕他连妾也不愿意娶了,只好费尽心思想了蜡人的法子出来—— “你们西凝山的蜡人,是怎么一回事,与书上说的一样吗?”淑莲终究有些好奇,那些在书里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书上怎么说?”反而是秀庆满面茫然来问她。 淑莲这些日子以来不知翻了多少书,她揪了一根长长的草叶绕在指尖上,“书上有一个不同的故事,说明初时候,西凝山有个蜡匠,不小心杀死了妻子的妹妹,为了求得他妻子的原谅,便用蜡制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出来。” 秀庆目瞪口呆,“……他的妻子原谅他没有?” 淑莲嘴唇边上泛出一丝浅浅笑意:“他弄错了,他的妻子其实早就死了。” “你讲一讲,我想听。”秀庆扬起面孔,越发显得一双大眼清澈明净,与她的姐姐秀馨有九分相似,“行不行,淑莲姐姐?” 指尖上的草叶一卷,堪堪拉出一道血痕,一大滴血珠子落在灰扑扑的土里,滚成了圆圆的暗红色一团,像是沉浸多年的血渍。 故事起源在很多年前收养鳏寡孤独之人的养济堂里。养济堂里有个孤女,幼年眉眼就比一般人生的好,长到六七岁,就是个显而易见的美人坯子了。美人自然受些优待,养济堂里的小子追着她跑,时时有人到她跟前来献殷勤。 她不过是个孤女,美貌使她有了优越感,这优越感叫她获得许多额外的帮助,叫她觉得安全,是她要死死抓住的东西。 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她的面孔渐渐长开,原先在右眼角一块毫不起眼的淡青色小胎记,不知不觉之中越长越大,越来越深,直至十五岁时,逐渐蔓延的印记已经覆盖右侧小半边面孔。她心急,私下打听良方,却始终无计可施,只能将乌发蓄留地更长,长长一缕自面颊边垂下来,将胎记挡住。 有一日,还是生出事端来。 那天她在池边提水,浇灌花花草草,遇到养济堂里一个有名的泼皮少年调戏。那人动手动脚来摸她面孔,她只怕被他扯开发丝见到那一块胎记,一时惊吓地纵身跳进冰冷的池水里。水居然十分深,她踩了两次没到底,想恐怕在劫难逃了。昏昏沉沉时,被一只手紧紧拽住了手腕。 养济堂里平素总与她做对的少女危难时刻将她拉起来,两人坐在石板上,精疲力竭。她正要开口道谢,突然惊觉少女诧异的目光正落在面孔上,心下顿时一凉——头发已经湿透拢到脑后去了,整张脸,没有一丝遮掩地呈现在对方面前。她一伸手,将这个不能被人知晓的秘密连刚刚救起自己的恩人,从石板上推下去。 一念入魔。 养济堂的人没料到她一个半大小女孩有这么恶毒的心思,把这件事归于泼皮引起的意外。但她怕,怕面颊上的印迹终有一天被人看到。她准备逃走时,她的姐姐从西凝山找来了。 西凝山上盛产白蜡虫,她的父亲郭氏经营一间制蜡坊,还曾为京师进贡蜡烛,名噪一时。她们姐妹出生时,有路过的方士说蜡坊终究会毁在她手上,父亲鬼迷心窍,将小小的她包裹起来,放在养济堂门前。母亲失去一个女儿,过不久抑郁而终,直至十五年后父亲弥留时,才将真相告知姐姐,她即刻就来寻了。 她们一胎双生,一模一样。 但她知道,她们根本是不同的。姐姐身边的男子替她将鬓发抿到耳后,她吹弹得破的肌肤上,白白净净,什么痕迹也没有。 她不动声色跟姐姐回了西凝山,乖巧地取得他们信任,拜在姐姐的未婚夫手下学制蜡。西凝山郭氏蜡匠懂得凝蜡换肤,凝蜡修补残肢。她十分有天分,又是自己人,不到半年就把修补面孔的方法学了来。 隔不久有一天,蜡坊的人都去山上祭祀蜡神了。 那晚起了大风。风似怒潮从西凝山的苍翠树海里漫过,整片山谷都回荡着凄厉哀怨的嘶鸣。 她在熬蜡房门口扭转开关,千斤重的石门缓缓打开,灼热的气浪扑出来。几十口熬蜡的大锅,上上下下错落地排开来。 她的姐姐,喝了她泡给的花茶,就靠在剥落颜色的墙角下,睡得婴儿一般。她拉她到蜡锅面前,将她的面孔按到沸腾的蜡汁里,热蜡覆上她的面孔,她的后颈起了巨大的水泡,晶莹剔透地一颗颗,珍珠一样柔美。 美人就是美人,死了也还这么美。 下半夜时,风刮地越发凄厉,她关上石门,盘起膝盖,手里拿着她的新面孔——刚刚从姐姐的脸上剥下来,这张莹润透亮的壳子下是淋漓的血迹,被满室热气蒸腾出诡异的香。她把它轻轻覆盖在面孔上,一丝不差地贴合——除了那块青色的胎记,她们本就是一模一样的。 她换了姐姐的衣裳,回到她的房里,在含苞梅花的清冷香气里安稳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用力摇她肩膀,“醒一醒!” 是他。 “熬蜡房……不知怎么坍塌了,滚烫的蜡汁流淌了一地,我们打开门,在其中看到,看到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穿着你妹妹的衣裳……” “她怎么会半夜去那种地方?”她假装失魂落魄,扯住他的前襟,泣不成声。 这个痴心又愚笨的男子,突然跪在她的面前,幼童一般失声痛哭:“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告诉她凝蜡修补身体的办法,她定是想自己试验,悄悄溜进蜡房,不料昨夜飓风,蜡房坍塌……” “你滚,滚出去!”她愤恨嘶吼,抽出琉璃瓶子里的梅花枝一根根摔在他身上,演到十分逼真,心里却为他的呆傻笑到要癫狂了。 新的蜡房很快修缮,但西凝山的人都知晓,因妹妹枉死,她性情大变,与他再也不复往日恩情。有一天,他突然来找她,叫她去旧的蜡房。 冬夜酷寒,漫天飞絮,是入冬来的第一场雪。蜡房坍塌后,石门边有条只容一人进出的狭窄缝隙,她跻身进去,一眼即看见破败的蜡房正中间那座一人高的蜡像。那面孔,分明就是她自己。不,是妹妹。不,妹妹就是她了。 “我将融了你妹妹骨血的蜡汁重新融化……再过七七四十九天她就能复活成人……这是师父都没有掌握的技艺,不是修补面孔,不是修补残肢,是铸造全新的人……” 她不知他在絮絮说什么,什么也听不清。她绕到蜡像的侧面,蜡像右面颊那里,不知融蜡时沾染了什么污渍,有一块淡淡的青色,牢牢地,阴魂不散地盘踞。 为什么要回来,回来的又是谁? 她一手推倒蜡像,蜡像磕在石门上,头颅轻易就折断了,掉下来摔地颅脑四分五裂。 她夺门而出,身后突然一声闷响,回头看时,他一头抢在巨石上,殷红的血迹自石门蜿蜒下来,染透了薄薄雪霜。 “我要怎样做,才能叫你原谅……”他似有泪,但面孔上依然是笑的,温和的,清淡的笑,一如那天与姐姐一同来养济堂时的模样。他们自马车上下来,站在养济堂简陋的大厅里,笑盈盈朝她伸出手:“来,接你回家了。” 她那时明明伸手过去了的,但已经回不去了。 这故事淑莲早看过,心里的震撼已经过去了,秀庆却是怔怔地,隔了很久,才用变了调的声音说:“她,太坏了。”秀庆长长呼出一口气,“做人怎么可以这么坏,她不会有好报。” 淑莲忽然有些不知所措。她要说的不过是这其中凝蜡成人的技巧,根本没有思考过人物的命运。太坏了吗?太坏了所以不会有好下场? 她慌乱地朝前走了两步,脚步不稳滑了一下,手指撑在地上,刚刚的伤口破裂开来,钻心似地疼。 秀庆坐在绣凳上,铜镜前点了两支白烛,烛台下缠了黑纱,软软地似一缕断发。 晚膳的时候,老太太又说,祭拜过姐姐再休息一天,然后就派人送她回西凝山。 秀庆有些惶恐,居然怎么都想不起来要回西凝山的哪儿去。不但想不起来住处,连自己以往的生活也记不起来了。脑海里模模糊糊的,只是姐姐秀馨的笑声:“秀庆,秀庆……”她温柔的手掌摩挲她的面颊:“好妹妹,你要好好的……” 好几天前,她确实是在西凝山下偶然听人说秀馨没了,一路打听,走到连家。但却不记得西凝山的事了。 不知坐了很久,烛火突突地闪烁起来,忽然有人叩门。一线细细的响声,似若有似无的风。 冬喜跟进门来,这么近地打量少夫人的妹妹,才看到她右边面颊上,靠近鬓发的地方,有一块小小的、淡淡青色的痕迹。冬喜噗通跪下来,朝她叩了一个头,实实在在的,额头磕在地板上“砰”一声响,“请二小姐帮我。” 她的右手伸出来,秀庆才看到她只有四根指头。 “婢子本来是少夫人那里服侍的,后来糊涂犯了错,被老太太责罚砸断了小指。婢子听说,听说西凝山的蜡匠能补好,求二小姐成全!” 秀庆惊愕一下,恍然明白她说的是表小姐淑莲白天讲的事情,她脑中混混沌沌的,冬喜又磕了一下,额头有血渗出来,“少夫人在世时跟奴婢讲过,西凝山确实有这门手艺。不但可以凝蜡补断指,补断臂,连制出完整的人也有办法。奴婢……奴婢才十三岁,不想就这么没了手指……” 她呜呜地哭,秀庆去搀她起来她也不理,只是求二小姐成全。秀庆满脑空白,只说:“你先起来,今天晚了,我一定替你想办法。”百般承诺,才把她打发走。 秀庆坐不下去,在连宅里摸黑走,想去找表小姐淑莲。她在这里谁也不认识,唯一说过两句话的,只有表小姐淑莲。她的样子秀气文弱,像是个好人,而且她知道些西凝山的事情,说不准可以帮到冬喜。秀庆凭着记忆摸索冰冷的青墙朝前走,一星两星刺骨的寒意落在面孔上,是落雪了。 她寻到那点光亮,舒了一口气,走近了想要推门,突然听里间有人说话。 “姑奶奶,侄孙女……不想嫁给他。” “胡说什么!他总会再娶,娶了别人,连家这富贵就没有我们一丝一毫了!” “……可这富贵,本来就不是我们的。” “怎么不是我们的!这就是我的!当初我辛苦盘算花钱请人半路上打死他们,从那时开始就都是我的了!” “哐当!”似是花瓶撞倒了,跌碎在地上的声音。“姑奶奶,您……您……” “话到这里,你若还是不想嫁,可别怪姑奶奶不留情面!” “姑奶奶……” 秀庆听着,不甚明白她们说什么,但这个响动,分明就是打起来了。她犹疑着要不要开门,突然听到“喀嚓”一声,似是木架被扯断了,隔着薄薄的窗户纸,火光呼啦窜起来,红彤彤一片。 起火了。 秀庆慌慌张张去推门,老太太果然和淑莲打了起来,那文文弱弱的少女敌不过看似枯朽的老妇人,被掐着喉咙摁在地上。衣架撞断了,纱绸披风坠下来,一角堪堪挂在青铜缠枝并蒂莲花烛台上,哧哧地燃了起来。这房里本来是又暖又干的,烧起来又快又烈,秀庆踩了几脚,火势越来越大,只好放弃灭火的念头,奔过来拉他们。 浓烟四溢,似挂了满满一屋子灰纱。 秀庆闭着眼去拉,拉到一只细细伶仃的胳膊,扯了就往外跑,到门外松开手,是淑莲,满面都是黑灰,从来锦衣玉食的小姐吓得魂飞魄散,好一会才醒悟过来,“姑奶奶,姑奶奶还在里面。” 秀庆头一扎,又进去。 浓烟滚滚,什么都看不见了。秀庆走了两步,脚下灼热,连呼吸也是滚烫的。她照着原路摸回去,突然被人一把拽住脚踝——“快,带我出去!” 老太太死死地抓住她,秀庆蹲下身拖着她朝外走,头晕目眩,整个身子都要燃起来了,但也不放,死死拉住她,一步一步。离门口还有十来步时,再也没有力气,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老太太却爬了起来,爬过软倒的秀庆,朝前爬。 下人们都赶过来了,正应了那句话“海龙王在也是扑不灭的”,门口的窗纸全烧起来,近前不得。 表小姐淑莲跌坐在门外嚎啕大哭,“姑奶奶,拉一拉秀庆,淑莲求您了……” 老太太心里在想,巴不得她这样死了才好。她奋力地往外爬,想到当初去找人来假装叛军枪杀自家老爷和大太太他们时,也是这样从城墙的狗洞下爬出去的。只要爬出去,就好了。 但她爬了几步便爬不动了。 衣裳下粘粘的,似拖了一层厚厚的油渍。她努力揉了老眼去看,袍子确实已经浸湿了,暗淡的红,似陈年血渍。滚烫的触觉开始出现在脚下,她拧头去看。倒在地上的秀庆,只剩下了半边脸。她的杏眼还在,依然水汪汪的,眼珠子还在转着,她右边面孔上一个淡淡青色的印记还在,但她贴着地面的另半边身子,已经融化了,桃红色半透明的东西在地上慢慢流淌开。 老太太颤巍巍伸手沾了一点,那一层东西在她苍老的指尖边流淌边凝固,成了一滴将坠未坠的血泪。 那是蜡汁。红色的蜡汁。 房顶的横梁突然“咔嗒”一声脆响,断裂成两截砸了下来。 烈火熊熊,外面清冷的空中雪絮还在一星两星地飞着,被火舌一燎,蒸腾地无影无踪,似从未出现过一样。 淑莲找到西凝山时,大雪已经下了三天三夜,漫天雪白。 她跟人打听秀馨,才知道原来那个绝色的女子是西凝山数一数二的蜡匠。很久之前,她的师祖郭氏还曾做过贡蜡进贡京师,那是整个西凝山的荣耀。 “妹妹?”那人蹙眉,“没听说秀馨师傅有妹妹啊。” 淑莲心里一滞,“叫秀庆的。” “哦,是了是了,差点忘了。”那人笑起来,“郭氏旧蜡房里存了一尊断了头的蜡像,出嫁前秀馨师傅把蜡像照自己的样貌修补好了,还给她取了名字叫秀庆,说是妹妹,替她守着西凝山祖业,蜡像本来就放在山上的祠堂里,后来不知被谁偷走了,再没有见过……” 淑莲一手捂住嘴唇,眼眶里突然盈满泪水,睫毛一颤,晶莹剔透的泪珠子滴在手背上,又烫又冰。但她什么也没说,走出门,朝着西凝山最高处张望。过了好一会,她掖一掖领口的裘皮围脖,深深呼一口气,转过身深一步浅一步地渐行渐远了。 扫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ongbailaa.com/cblxgls/7972.html
- 上一篇文章: 核桃树皮的功效与作用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