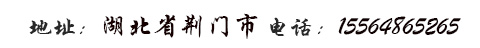故乡的树
|
故乡的树 早晨上班,骑车行于中河边,忽然一阵甜甜的花香扑鼻而来。好熟悉的花香,虽然我知道,这肯定不是洋槐花的香味,而应该是柚子花的花香,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洋槐花。 回忆,往往会被一个名字、一首歌曲或一幅画面所唤起,这次唤起回忆的是丝丝缕缕的花香。 回忆,往往是纲举目张,一旦拎起来就带起来一连串儿相关的记忆,彼此不能分割。 所以,在说洋槐花之前,我想先说说家乡的树。 论及品类之盛,北方的树木品种是远远比不上南方的,尤其是在老家那片广袤的黄河中下游平原上。但在三、四十年前,我老家那儿树的种类比现在要多,具体原因不太清楚,也许这仅仅是根据一种不太正确的印象作出的判断,也许是因为老家的群众越来越注重树木的实用性和经济价值,有些树,人们不再去栽种了。 在家乡,杨树,柳树,是数量最多的,这些树木经济价值高,成材也快。我们那儿栽的杨树在植物学里细分的话叫什么名字,我至今搞不清楚,我们那儿都叫山杨,也有叫钻天杨的,但我觉得更像是响叶杨。至今记得特别清楚,在炎热的夏天,吃过晚饭,搬张凳子坐在院子里乘凉,看稀星朗月,时有细细的阵风吹过,院子外边的杨树叶子立刻就哗啦啦地响起来了,像小孩子在拍手,所以我觉得称为响叶杨这个名字应该更确切也更有意境。杨树很高,杈少,叶大,叶面光滑,呈心形,可折下来喂羊,羊喜欢吃。杨树春天开花,它的花像毛毛虫一样,植物学上应该称之为穗状花序,紫色,可食,好像我幼时曾经吃过,洗净后加油炒的,但已记不起味道如何了,好像不苦。也有大白杨,树皮白,树干直,长得慢,其叶背面有白色短毛,喂羊羊都不喜欢吃的。柳树,曾经是我们村里最多的道旁树,我能记事的时候已经有一抱粗了,不知是什么时候栽的。我们村的这种柳树不是垂柳,不像垂柳那样有绵长而下垂的枝条,所以也不会让人触景生情吟出“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的缠绵句子。后来,差不多在我初中的时候,这些柳树都卖掉了,换种了杨树。 曾经有段时间我们老家栽了很多桐树,我一度以为这是梧桐树,因为别人都称之为梧桐,其实不是,它是泡桐,引不来金凤凰,也做不得焦尾琴。这种泡桐树长得很快,但年数长了树干会有中空现象,木质松软,锯出来的板材都架不住成年人的指甲去抠,一抠一个指甲印,因为太软,不能承重,只可做板材,叶子硕大,像小蒲扇,开紫白色喇叭状的花。泡桐多栽种在田间,是经济树种,也有栽在家里的,因树冠大,叶子大,能遮荫,但又影响晒衣服晒被子,挺矛盾的。 有椿树。其中香椿的嫩叶可以食用,是一种美食,可炒蛋,也可腌了拌豆腐,现在还有些人家种这种树。还有一种椿树叫臭椿,叶子有股臭味,开细碎的花,也有淡淡的臭味,花后结荚,像扁豆,有种子数粒。这种臭椿好像很少栽了。 小时候,邻居家院子里有一棵楝子树,不知其学名是不是楝树,春末开花,香气馥郁,百步可闻。小时候的有首说节气和农时的歌,其中有这么一句:“楝子开花提蒜薹”,以此可知其花时。后来这棵树被伐了,从此再没有见过这种树。 村里有一棵大楸树,合抱粗细吧,立在村委大院前的主干道路上,有点碍事儿。这棵树也不知是何人所栽何时所栽,我小时候它已经死了一半了,因此树冠很小。因为树太老太大,因为它还有一半是活着的,村里人就认为有神灵住在这棵树上,无人敢以斧锯临之。 我们村里有几棵桑树。在我小时候,村西有一棵比较大的,在第六生产队打麦场的边上,差不多碗口粗细,在我们看来此树不祥,因为一男青年和父母吵架后在此树上上吊死了,事后我们小孩子都去看,但没看到尸体,也幸好没有看到。村北,也是在打麦场边,另一生产队的打麦场,也有几棵桑树,粗细略小于碗口,初夏时结红红紫紫的桑椹,不是很甜。当时我上初中,走读,上学放学都经过的,懒得去采,因为自己不善于爬树,也因为它们结的桑椹不好吃。我们村里桑树不多,在我记忆里就这么几棵,但别的村应该有专门种这种树的,因为我们那儿有种叫做“叉”的农具,麦收时必备农具之一,就是用小桑树做的,称之为“桑叉”,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几乎家家都会栽一两棵枣树,收下来的枣子主要用于过年时蒸花糕。枣树木质特别坚韧,是很好的木料,但因为枣树都不粗,做不了大家具。小时候,老家农村是有纺车的,手摇的那种,一只手摇车,一只手扯棉絮,就把棉絮变成棉线绕在锭子上了。“锭”字,是金字旁的,但老纺车的锭子却是木头做的,用的大都是枣木,耐磨。纺车的其他部件,像摇柄、轴,也是易损部位,也多用枣木。 有的人家会在院子里栽棵石榴树,“五月榴花照眼明”,红红火火的,而叶片绿浓欲滴,如此红绿相映,十分悦目。石榴花开的时间很长,开着开着就看到小石榴越来越大,中秋时石榴就咧嘴露籽了。 桃树、梨树、杏树、柿子树、苹果树,这些果树在农家庭院里是很少见的,也许曾经有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有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运动,农家院里的果树都遭了殃,被砍伐殆尽。庾信有诗:“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句话反过来说倒是刚好配得上那个荒唐的时代,“人犹如此,树何以堪”,人都被整成那个样子,何况几棵树啊。不过,我们村里倒是有个集体果园,每年家家户户都可以分得到苹果的,但桃、梨、杏、柿子就不曾记得有分到过,也许产量太少吧,一个庄子两千多人分不过来。因为村里果树少,果树的花期又短,所以我到初中时才第一次看到杏花,当时认为杏花是最美丽的花,未叶先花,粉瓣红萼,中心是密密长长的花蕊,比芍药花美,那种惊艳的感觉至今还印象颇深。 老家有尚武之风,村里练武的人家里大都有几根白蜡杆子,可单用,做棍,耍起来呼呼带风,也可以安上枪头缀上红缨。表演钢枪刺喉用的枪就是用白蜡杆子做枪杆的,可弯曲至满弓状。这种白蜡杆子是取一种小树的树干制成的,这种树也叫白蜡树,极直,极柔软,又极坚韧,据说我们邻近乡镇的林场有专门栽种的,但我没见过活着的树。 榆树,在北方曾经广泛种植,与人关系密切。小时候我家里就栽了好几棵榆树,是父母刚搬到新院子时栽下的,那时我可能只有两三岁,而卖掉其中最后一棵榆树时我都已经参加工作了,长了二十多年,算是和我一起成长的,我长大了,它们也都成了栋梁之才。榆树木质坚硬而韧,民间形容一个人愚笨不开窍或者顽固不化就是用“榆木疙瘩”这个词,可见其坚韧程度。榆树是做家具的好木料,也可以做房梁。榆树的叶和树皮,是可以在饥馑之年充饥的,我奶奶、我母亲那代农村人都吃过的。榆叶可以蒸窝窝头,树皮好像要磨成面吃的,母亲应该说起过。据说年前后榆树死了很多,原因就是人把榆树皮给扒光了,一棵棵榆树就像被扒光了衣服的人,赤条条地立在那儿,满怀着无声的愤怒、绝望和悲哀。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但这句俗话只对了一半,人不要脸还可以活,而且一旦脸都不要了反而能活得更舒坦,但树没皮就会死。另外,我想把“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句诗再说一遍,虽不合原意,但仍然觉得十分贴切:树都被人吃成这个样子了,人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一时期饿死了很多的人,据说有几千万。 据说老年人说原来榆树是不生虫子的,后来因为缺粮,国家进口了美国的黑小麦,就带进来一种专门祸害榆树的虫子,叫榆蓝金花虫,学名叫榆蓝叶甲,不知道其原产地是不是美国。这种有个很好听名字的虫子很让人恶心,作为幼虫,其形如蛆,背黑腹黄,乌压压地在树皮聚集成片,啃食树皮,致汁液顺树皮下流,有密集恐怖症的人是吃不消看的。若拿瓦片、砖头或鞋底盖在那片幼虫上往树干上压,一股黄粘的液体从死虫的身体里冒出来,顺着树干往下流,像粪汤,恶心极了。待其变为成虫,仍是专吃榆树的叶子,把树叶咬成网状的残骸。在夏天,农民们喜欢在院子里边乘凉边吃晚饭,这种虫子见光而至,啪啪啪地落下来,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虫子,用落虫如雨来形容不算是夸张,有时会落到饭碗里,让人不胜其烦。因为这种虫子,现在农村栽榆树的人家已经非常少了。 春天,在榆叶将发未发之际,榆树的枝条上会冒出一簇簇一串串的榆钱儿,顾名思义,其状如铜钱,那是榆树的果实,学术上称为翅果。新发的榆钱嫩绿嫩绿的,可食,奶奶曾经捋了和入面粉做成窝窝头,吃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味道,有点粘,不如捋下来生吃,有淡淡的甜味。据说现在有人吃厌了大鱼大肉,开始回归乡土田园,用榆钱来做粥,也有加白糖凉拌了吃的,味道如何,不得而知,如果能在榆钱刚上枝的时候回趟老家,或许可以试一试。榆钱老的快,过不了几天就不能吃了,待其发黄,纷纷离枝,飘得满地都是。偶有榆钱会在水土适宜时发芽的,随地长成一棵小榆树。 好吧,现在开始说说槐树和槐花。 槐树,在我们那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槐,是我国的传统树种,据说国槐是西安的市树,可见当地国槐之多。《千字文》里那句“路侠槐卿”里的槐,就是指国槐。中国古代对槐树是怀有崇敬之心的,朝廷上的三公就被称为三槐。国槐开花较晚,是夏季开花,花骨朵可以采下来晒干入药的,称为槐米。我见过村里人晒槐米的,不知道价格如何。城市里经常见到的龙爪槐,较常见的国槐个头矮,树冠像把伞,叶、花都和国槐别无二致,其实是国槐的一个变种。另一种槐树是刺槐,我们那儿称之为洋槐,原产地不在中国。洋槐树形高大,枝条有刺,木质坚硬,成材后可做盖房的梁檩,也可做家具,特结实。 我们老家种的槐树大多是洋槐。每年的春末时分,村里的洋槐开花了,树叶藏不住,白花花的一树,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花香,直沁心脾,让人的心情也欢快起来。这种槐花的香气是一旦嗅到一次就毕生难忘的,特别像江浙一带柚子树的花香,甜,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甜,甜而不腻,比秋天的桂花还甜,但不如桂花香。洋槐花也是重要的蜜源,槐花蜜是比较甜的一种蜂蜜。在洋槐树多的地方,总会有闻香而至的放蜂人。不但对蜜蜂,对人来说,洋槐花也是种诱惑。耐不住了,有人就会把镰刀绑在一个长杆子上,去把开着花的小树枝削下来,然后把槐花捋到一个高粱莛子做的筐里,去做菜。我小时候,村里的槐树多,每年春天母亲都会捋一大筐子槐花,先加盐揉了,然后和在面糊里,在锅里加油煎成饼,两面煎,油多,还脆,香中带甜。如果干吃槐花饼吃厌了,也可以把饼切成小块,放在开水锅里小煮一下,然后带汤舀入碗中,放点酱油、醋,是另一种风味。洋槐花也是可以生吃的,像榆钱,但比榆钱更甜,口感也更好,当然,看起来也更好,这才是传统意义上的花啊,榆钱都不像是花。 一晃眼的工夫,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在老家过春天了。不知每年那阵甜丝丝的花香弥漫在空气中时,母亲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把镰刀绑了去摘槐花,去煎一顿槐花饼。但我知道,每次在江南闻到那甜丝丝的花香,我都会误以为那是洋槐花在盛放。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会忽然感觉到故乡在等着我回去,故乡的树在等着我回去,母亲在等着我回去。 毕于-5-15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ongbailaa.com/cblxgpw/415.html
- 上一篇文章: 防暑降温药品清单
- 下一篇文章: 上海市病虫害预测预报绿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