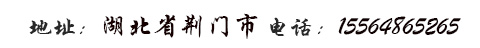散文天地毛万安又是芒种夜雨时
|
毛万安,汉族,年生,~年北京当兵,退伍返乡务农、打工,自幼爱好书法、诗文,公开出版有诗文集《春天的旅行》。 又是芒种夜雨时 ●毛万安 大雨敲打着雨篷,大风摇晃着小叶榕,阳台上开得正旺的栀子花,香气随风透进纱窗,从躺下一直到天亮,风雨一直没有消停,我总是想着那个场面,总也无法消停。身边的她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们想说说话,必须压过风声雨声。声音太大,又担心影响二楼四楼休息。同一位置,二楼是幼儿教师,四楼是乐山一中的物理老师。呼吸着雨中栀子花香的空气,我反反复复地追忆回味着。 年,也是这芒种天,78岁的父亲起早上山采桑叶,腿摔伤了。两张小纸的三眠蚕儿,已经布成了四簟,还有八只箥箕。母亲惊慌了,赶紧差人进城找我,我立马请假,老板不同意,我立马就辞职了,还有一个月元工资,我不要了。我借用鼓楼街税务所办公室的电话,向厂的大哥报告父亲摔伤的情况。大哥说,虽然你工资比我高,你要清楚你是被聘,不是正式工,你辞职回家照看父母是正确的,还有16年我就退休,我退休回去接手,你再出山。其实,不用大哥说,我早就有了辞职回家的念头。 那几年的蚕茧卖得笑,每季蚕儿大眠起来,我都习惯了要请四五天假,还有栽秧打谷,我也要请四五天假,老板都支持。这次是老板娘装了怪,我就反炒了她的鱿鱼。父亲在解放前就是养蚕高手,解放后干了几十年蚕桑技术员,一柜子的奖状奖品。父亲年生,3岁就死了爹。奶奶娘家是吃得起饭的,自家有缫丝作坊,榨油坊,还有砖瓦窑,山林土地上百亩,一年四季都有长工。奶奶读过不少的书,爷爷死后,她一直不嫁,全靠娘家周济,守护着父亲这根独苗苗,守护着二十多亩山林和两三亩田土。我幺舅公为几个儿女和我父亲开了私塾,几个表叔和我父亲边读书边劳动。养蚕缫丝,挂虫子熬白蜡,煎菜籽榨油,踩泥巴做砖瓦,我父亲都是一把好手。解放后土改,幺舅公成了地主,我家是贫农。乡亲们都说,单凭我父亲的字墨完全可以当乡里区里县里的干部,可惜舅舅是地主,土改工作队只给了他一个互助组组长。后来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他一直都是蚕桑技术员。由于父亲是劳模,我的幺舅公历次运动都没有挨过打,他特别喜欢精编篾货,他编的扇子、提篼提篮人见人爱,他活到了96岁,去世前三天还在编。幺舅公的孙女的女儿在青神竹编工艺城编织百虎图、百帝图和清明上河图,荣获了国家中级技能四级证书。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两家人一直来往密切。去年我的朋友编导《竹韵天下》,我去青神表妹家,我想写我侄女的竹编,表妹说,你最好先写表叔,表叔更值得写。他的表叔就是我的父亲。 年土地下了户,家家户户都喂蚕,全村的人,外村的人,都来请他给蚕儿看病,他老人家压根儿不取分文。父亲还有三样绝招出了名,一是嫁接各种果树十拿九稳,二是穿牛鼻子牛儿顺善,三是搭担教牛牛好使。这三招,也是村里村外几乎包干了,也是压根儿不取分文,几十年一路走来,十里八乡,父亲的人缘特别好。 父亲躺倒了,我顾不得一切了,骑着永久加重,心急火燎飞速回家。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个个都已成家立业,二老还是这么辛劳。眼看就是80岁的父亲,还如此爱蚕如命,很多人都不理解。双老拉扯我们五兄妹长大成人建家立业的艰难苦楚,我最清楚。二老还有43个干儿干女,年年正月和生日,一切人亲往来,从来不要儿女分担。乡亲们都说我父母天性好,带儿女不损失。二老最大的干儿子是抗美援朝的大英雄,最大的干女儿是医学院的专家教授。大大小小的干儿干女多数都出去干了事,有出息,回来都要来家看望,向干爹干妈摆谈外面的大世界。父亲70大寿生日宴上,有人专门考证说:“43个干儿干女,没有一个干坏事不争气”。年,我和大哥同时考兵录取到成都部队,公社要求我第二年再走,要我协助家庭,让弟弟妹妹再长大一岁。年,父亲以劳模身份找公社武装部,要求他们兑现承诺安排我再考,结果我就去了北京部队。父亲向公社大队承诺,如果家庭年终决算倒差,绝不吃国家和集体一分钱补助。在我心目中,父亲滚瓜烂熟的四书五经没有白读,他的为人处世,够我想一辈子。 一进蚕房,我惊呆了。堆成了山的桑叶,足够吃三天。父亲的腿肿得厉害,一手拄着掍子,一手摆弄着他心爱的蚕儿。母亲说:“这全是乡亲们送来的叶子。”其实不用她说,我一看就明白了。 真是祸不单行。我刚辞职回家的当天晚上,就是昨晚这样的大风大雨,我家左耳房后边山体滑坡,至少三四百立方土石,厨房猪圈牛圈堵紧了一半。两个沼气粪池水漫金山,半条石半土砖的后墙全部移位,推进屋里的土石顶住房梁,房上的瓦震落了一多半。万幸没有人畜伤亡。幸好我刚回来了,幸好我曾经是军人,参加过多次抢险救灾。这次自家摊上了,我便从蚕房转战到耳房。百米之外的邻居胡仲仁大叔,听见这边的巨响,也及时跑过来参战。胡大叔是抗美援朝老兵,我们两家,从来就是一家亲。 天快亮了,风还在刮,雨还在下,我坚决要求胡大叔回去休息。他已经63岁了,我怕他累倒了。他老伴得胃癌才走了不到三年。他的两个女儿,都是我的干妹妹,都外出打工了,我怕累倒了他,没法跟干妹妹交待。 天亮了,风停了,雨小了。八点钟了,我们正在蚕房忙活,突然来了大队人马,啊——是胡大叔去报告了。全村的党员团员都来了,村长村支书领头,五颜六色的雨衣雨披,还有蓑衣斗笠,全都自带着工具。看见这阵势,我的母亲哭了。我劝母亲不要哭,赶紧去胡大叔家打理烧开水煮饭,我得赶紧去两河口买烟,抓几个弟兄安排安排。支书说早饭都已经吃了,中午大家都各自回家吃。我说中午晚上不吃我的,这活路就谁也不要干。村长支书只好依了我。 仅仅一天工夫,三四百立方的土石,全部被请到了院坝外边,堆成了一座小山。滑坡下来的二十几株栀子花,是我和她谈对象时栽的,母亲一直都是精心料理,这次滑坡,又是母亲指挥,全部移栽到了新堆的小山上,几位团员姑娘媳妇,争先恐后挑来清水,把枝叶花朵骨朵儿上的泥浆,冲洗得洁洁净净。我家厨房后边这些栀子花的故事,乡亲们家喻户晓。我奶奶97岁过世之前,她一辈子的爱好就是珍藏虫屎茶和黄栀子。虫屎茶就是生了蛀虫的老人茶,黄栀子就是栀子花谢了结出的果子。虫屎茶治饱胀病,不管是人还是六畜,保证见效;黄栀子治人的懒黄病,就是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肝癌,还能外用敷疮。十里八村的人,凡是要用这两样东西的,全都到我家来求,我奶奶从来不收分文。我第一次带着女朋友回家探亲,正巧碰到有人来我家求黄栀子,她说奶奶这么大年龄,又是小脚,上山寻找采摘黄栀子不安全,我俩为奶奶栽一块小地吧。于是,就有了这一片栀子花。真没想到,天灾来了,母亲还这么重视,几位团员姑娘媳妇也这么上心。 这一天,我请来了厨师,安排了打杂跑腿的弟兄;这一天,我飞快地写了多字,乡广播中午晚上都在播;这一天,我的精力,我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晚上九桌人喝酒吃饭,我端起酒杯向乡亲们深深鞠躬,一桌一桌挨个儿敬酒,感谢大家在这百忙之中放下自家的活路冒雨来我家救援。我清楚这芒种天,昨晚下了通夜大雨,许多望天田终于可以引水整田栽老秧,可惜好些人都放弃了良机……大家都是农民,我没有多说,一切都在这酒杯里了。我敬到了村长面前,他当众宣布,要我写个申请报告,补助元修补受灾的房子。我父亲力撑拐杖站起来打断村长说:“心意我们领了,钱我们分文不要;申请要写,我要砍几根杉条整蚕架蚕边子,请乡政府批几根树子的砍伐证”。父亲的发言刀砍斧切,九桌人立刻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昨夜我彻底失眠了。这个场面,这些人的面孔,总是挥之不去。今年清明我回去,我的那一片宅基地,早已变成了花椒林,院坝边假山上的那些栀子花,也全部换成了花椒树。我仔细打听,当年帮我家义务抢险的,那86位男男女女,健在的还有38位。我站在花椒树丛中的假山石上,突然想起了好友雪川的诗句:“不要说这是绝版/也不要说这是让后人铭记的写真/都市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日子都装订成野史/哭声里都有笑声”。我要说,都市和乡村都是如此。 不知为什么,无论在哪里看见栀子花,我就会想起那个场面。凡是刮大风下大雨,特别是夜里,我总是要失眠,总是要想那个场景,彻底失眠,昨夜才是第一次。正是:打工进城蜕农皮,满怀乡愁自由诗。如烟往事难忘却,又是芒种夜雨时。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作家协会主办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ongbailaa.com/cblcjjg/1984.html
- 上一篇文章: 芷江民间故事十五白蜡的传说
- 下一篇文章: 6月2324日漫步在白蜡湾山海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