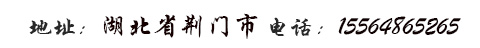舒丹丹诗三十首
|
舒丹丹:诗三十首 松针 在梦里,我走上常走的那条山路 在一棵松树下,痛快地哭 那哭声,好像把紧裹的松塔也打开了 我太专注于自我的悲伤了 以至我忘了这是梦 以至我没有发觉,身边的松树 一直在沉默地倾听 将它细密的松针落满了我的周身 我醒来,已记不清松树的模样 但那种歉疚,像松针一样尖锐 秩序与悬念 傍晚的厨房,让她想起祖母的厨房。 一样的夕光从窗口涌入,锅盆碗柜各有定局。 炉火生动,菠菜已洗净泥土。 她站在火炉前,等待一钵土豆慢慢成熟。 这逼仄的空间里已无悬念, 该完成的已经完成,进行中的正在进行, 生活的秩序正展现它清晰的面容。 她会在这厨房里,老成祖母一样的祖母。 她感谢这一钵土豆,给她短暂的出神, 让她像个局外人打量她措足的方寸—— 杯盘洁净,瓜果安宁,它们在寂静里获得神圣。 她甚至感谢这时从窗口掠过的一只鸟,从最深的秋天飞来, 在密实的香气里,带给她一瞬间 振翅的幻觉与虚无。 庭院 去菜场的路上,总经过一座庭院 铁栅门虚掩着,野草安静地生长 我放下装满蔬果的菜篮 在石阶上坐下 仿佛一瞬间就从俗世中抽离 头顶的樟树像升腾的绿火焰 把我拢在它的宇宙之下 从栅栏间我打量路过的麻雀 从蒲桃花的轻柔里触到婴儿的呼吸 与黄昏的宁静一同洒落的 还有虫声,潮气 和闪烁的内心的光斑 多么好,这片草地,这个时辰 一种缓慢,纯粹 独属于我的一种好的孤独 或者丝毫不觉孤独—— 我深陷在樟树的浓荫里 与一个看不见的声音独语,对白 一枝一叶,搭建一座云中的庭院 没有人知道这种虚构和专注 带给我怎样的意义 月夜闻鹧鸪 溪对面的山崖上 瀑布在唱歌,在月下 溪这边的人儿,睡着了 梦里头听见鹧鸪声 一只鹧鸪住进身体里 心儿飞过柳树梢 随你骑马过山崖,随你撑船 下河滩,掐一把虎耳草绿莹莹 歌声再好莫当真呦 今天唱给你来听,明天唱给别人听 溪对面的瀑布,唱了三年零六月 溪这边的月光,碎了一身 安静时就能听见它们 春天里站在窗口的这棵树,秋天时,还在。 整整一个夏天,没有走远,也没有靠近。 有月亮的洁净的晚上,能看见星星。 但在黑夜,或阴沉的白昼,星星们也在。 早起听到鸟鸣,知道鸟儿藏在木兰枝里。 但这些下雨的清晨,鸟儿们和木兰一样安静,它们飞去了哪里? 原谅我,那么长的时间里,我只知道 季节的诫命让树木学会了舍弃,从未想象 泥土中它们无法动弹悲欣交缠的根。 我的眼睛太久地习惯了太阳和月亮,从不曾闭眼 倾听过沉默的星辰。原谅我第一次知晓 下雨时鸟儿们从不闪躲,它们在风雨的巢中 垂头敛声,隐忍得像群苦行僧。 野鹿 鸟羽有风,松林上有薄雾 夕阳的金手指正抚摩群山的脊背 一棵白蜡树的牵引让山崖躬下身子 俯看脚下两只悠闲的野鹿 我们停车,在松针的阴影里呼吸、倾听 沉陷于周遭渐渐聚拢的黑暗 湖水微漾,神似一种天真 无边的静穆,近于本我 在山野,生命各领其欢,纯粹而自由 如心灵盛开,如鹿垂下眼睑 孤独的约书亚树 荒漠和天空之间 这些树在奔跑 这些有着圣徒名字的约书亚树 它们虬曲的枝条,像一种挣扎 挣扎中向上祈祷 每十年一英寸,它们的生长如此缓慢 慢到让你确信,它们并不急于获得高度 所有进入过枝干的阳光,水分,和沙砾 最终都会渗入根须 在暴烈和严寒的时刻,成就生命的真相 它们守着脚下的砂石,一棵树 遥望另一棵,一棵树,望不见另一棵 把自己活成一块活化石吧—— 在这速朽的世上,孤独是应该学会承受的 真理。看,它们挥舞的手臂仿佛在布道 “抵抗死亡的唯一保护 是爱上孤独。” 夏日牧场 正是午后时分,远山沉静 背阳的一面,山气酝酿着幽深的蓝 天空收留了云朵的流浪 丝柏树像从泥土中喷涌而出 把它浓郁的生长泼向空中 这是蓬勃的夏日 青草气息浓烈,两匹马 低头咀嚼,或交耳亲吻 以它们温柔的爱喂养这片心灵牧场 云朵之下,没有孤独的人或破碎的梦 万物都沿着各自的生命经纬 在奔跑,像世界的初始和终极 像尘世隐藏了悲喜和纷扰 只有时间站在局外,如神手持权杖 俯望并接纳一切 琥珀 如果细嗅, 封存的松脂的香气就会逸出, 秋天就会降临, 月光就会带来一只蜘蛛和蕨草的私语, 你就会看见老虎的魂魄, 和时光金黄的肉身。 如果将一块琥珀戴在胸间, 白垩纪的风景就会全部复活。 与海浪鸥鸟共度一个下午 面对大海尽可放弃言辞, 平静或激荡,都有海浪替你说出。 只需走进薄薄的潮水,加入到 那网一般倾覆的鸥声中, 立定,看细浪一遍遍安抚沙滩, 远处一只鲸鱼突然喷射水柱, 撕开海面柔软的蓝绸。 或者踢掉鞋子,当潮水收拢夕光, 与奔跑的影子追逐, 偶尔被贴地而生的海草或贝壳 轻轻扎一下,如同遭遇生活 暗藏的尖刺:一切都是馈赠。 仿佛听从一种神秘的自然教义, 巨大的美与安详将你俘获, 令你噤声,失忆—— 没有痛苦值得想起,也没有夙愿 需要许下。直到天空矮下来, 鸥鸟栖落又飞起,为你停留在 一个合适的高度。 秘方 白芷,白芨,白芍, 我确信,都是世间的好东西。 洁净,清心,活得小心翼翼, 零落成泥,磨成齑粉, 据说,能让美人脸上开出一朵白山茶。 我惊讶于另一种智慧:这秘方里还需加进 白僵蚕,白蒺藜,白藓皮—— 一些更为粗粝、尖锐,甚至死亡的东西, 像温柔的凝视里 有将你的心咯得生疼的坚硬, 或薄雾的面纱下,嶙峋的真理。 它们同样与美发生光合反应, 生成微蹙的眉,隐秘的刺痛, 白茶花心中不可逼视的阴影。 元宵纪事 今日元宵。早起揉糯米粉,甜酒煮汤圆。 收拾衣橱,找出去年的淡青色旧衣。 窗外橘花犹盛,斜眼看,旧枝又着新蕾, 黑猫携白猫跳过篱墙。 傍晚记起母亲教导,打开家中所有的灯, 今晚每个犄角都须亮堂。 季节与生活赐予的一切,原不为写诗。 在风俗中老去的人,内心如城池安定。 夜来无事,灯下展读《十一种孤独》, 惟此一点,不合节日气氛。 黄昏重读格雷厄姆 那些“越过美,和美的傲慢”的鲑鱼 那些神秘的米诺鱼 一瞬间,全都游过来了 越过时间的漩涡,越来越近 越来越清晰—— 它们没有被虚无的泡沫湮灭 也没有被激流冲散 它们游向自身 游向更深的自由 那个春天,我暗暗攒劲 为它们在纸上建一座大海 我曾以为什么也难不住我 就如同我也曾愿意为你建一座大海 但一个小小的瞬间就打败了我们 只有这些鱼儿还在游着 在独属于它们的深海 即使生命的诡异让人痛苦地闭上了眼 什么也不想说 只静静地听着水流的声音 我也知道,它们仍旧游着 在独属于它们的孤独和意念里 风停了 ——观一场装置艺术 无叶风扇呆立在墙角 安静得很无辜 仿佛它的身体里并没有叶片转动 但谁都知道 风是从那儿制造出来的 像一种感官刺激 玻璃房里千万只红色塑胶袋 蜂蝶乱舞,飞上半空 被牢牢吸附在天花板下 一种近乎狂热的视觉冲击 风的速度让它们失心疯地打开自己 在扭曲的飞旋中发出轰鸣 犹如失控的语言—— 紧张,神秘感应,虚无宇宙中 复杂的心灵投射 在一场关于生命的故事里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忽然,风停了 蜂鸣声戛然而止 虚拟的飞翔从半空中跌落 世界骤然坍塌 它们匍匐着,瘫软成一堆死灰 如烈焰燃尽的虚弱 如冲突后的静默时光 高速公路上一匹伏地而死的马 极力回想它的样子,它鬃毛的色泽, 它倒地而卧的姿势, 但是很难。它整个的存在像一团雾, 模糊,难以辨识。汽车箭一般驶过, 并未为它片刻停留。“它死了!” 这样的念头,比雾更确切。 一切都和从前一样。草场静寂, 风声并未改变栅栏。 同伴们仍在低头吃草,或交耳轻语, 没有谁发现,马群中已少了一个; 而它卧在这里,再没有奔跑和嘶鸣, 身旁已奏响苍蝇的圣歌。 没有人知道,它是因衰老而气绝, 被最后一根稻草压死, 或是带着对未知的向往, 扬起双蹄,踏破尘土, 在跨出栅栏心神驰荡的一刻, 被突如其来的飞车掀翻在地? 像固有生活的厌倦者和僭越者, 它纵身一跃,脱离了它自己—— 仿佛灵魂出窍,影子想要跨出躯体。 来不及说出最后的渴望 或悔恨,它闭上了它忧伤的眼, 安静得像是,一个代价。 倾听 夜色从细叶榕的枝间滴下。 幽暗里,一条小径呈现出自身。 有一些超越白昼的声音。 隐藏在草丛的鸟儿噗地飞起, 翅膀后面,是惊讶的天空。 从远处望,万家灯火都很安静, 浮世在黑暗中变得虚无。 在这渺小的夜里, 面对寂静和内心,无话可说, 只想成为一个倾听的人。 仅仅是倾听。 神农山,或朝圣之旅 据说,春蝉为此山独有,白皮松也是, 如果盘旋于山顶的那只苍鹰也可以算上, 为什么只在此地—— 细想,仿佛一种让人感念的 长久的执意。 山脊上,石阶枯瘦,草木 明亮而自足:鹅耳枥,壳斗科,蚂蚱腿子, 在相识之前,我先爱上了你们原始的气息。 山路如世路,我用发颤的脚步 练习一场漫长的朝圣。 坐下来,在通往紫金顶的山门前小憩, 蝉声交织风声,如一张缜密的网。 一个我,回望另一个我, 多么弱小,眼前这一脚,是踏进窄门,还是 遁入空门,似乎已不是信仰问题。 此去苍莽,有多少浓荫和光照需要领受, 才能像一棵树在悬崖上孤独地站定—— 紫金顶上,我探问一棵白皮松的年龄, 但它以三千八百年的沉默,对我 置之不理。 “你的前世是一只孤傲的羚羊” 对于风吹草动,和潜在的危险 你有本能的机敏 你迅疾如闪电的速度,甚至可以媲美 一只追逐的猎豹 你躬身一跃,就能逃离现场 你的冷静,总能让你 全身而退 作为一只羚羊,你怯懦而刚强 你的孤傲像荒原上的针茅草一样尖锐 你有致命的弱点 为何总在奔逃的中途停下,回过头 深深凝望?—— 这深深一瞥,泄露了 你全部的破绽和对世界的纯真 这一派清波也是我的源头 ——在边城遥念沈从文先生 在沅水,跟随一条小船 转柳林岔,泊鸭窠围 看尽那一点寂寞的山水和林梢 就到了叫作常德的码头 这一派清波也是我的源头 我也曾站在这样的甲板和渡口 看艄公在暮烟里拉篷,摇橹 无穷无尽地往来于此岸和彼岸 是什么时候,橹歌已消失 河底的流沙改变了它们的航道 那长着黑翅膀的鬼脸蜻蜓 早已飞入没心没肺的水草 唯两岸的吊脚楼仍守望着河水 庄严地忠实于它们的“分定” 唯烈而痴的血性与爱恨,仍一点就着 如渔火,在这条河上流淌 从你的脚印和文字里看见的预示 已在时间身上一一印证 生命的困境一如你的年代,总悬在 美善与不能诉说的悲苦之间 在渡口,无论我的眼睛 湿成什么样子,都唤不回那条渡船 我把手伸进水中,在秋天 沱江的水仍是温热的 平衡 香气是它空中的路径, 一只蜻蜓悠然来访,落在我 举起的手机上,练习平衡术。 我用手机的眼睛看风景, 它用黑骨碌的眼睛瞅我。 它是来端详影像中的自己,还是为了让我 在它千百只复眼中,辨认千百个的我? 有一两分钟,它静止在一个支点上, 在抓握和伸展, 警惕和松弛中,获得平衡, 仿佛身体睡着,灵魂的羽翅 却仍在作梦。午后的深林有清凉的安静。 我们在众目睽睽下 交换丰富的眼神,那一瞬有如神迹, 充满信任和交会,不可言说。 我与它又对视了两秒,然后抖动手腕 提醒它飞走。它消失在 来时路隐秘的香气里。 路遇收割后的稻田 这是收割后的稻田,它的丰饶 属于上个季节。它已过了扬花抽穗的日子, 谷壳已走向另外的用途。 我并不怀疑稻田的前生,每一颗被遗忘的谷粒 都反刍着光阴。我站在凛冽的事物中间, 捕捉到最寒凉的空寂。如果空寂 触手可及,空寂前的饱满也曾溢出浆液。 关于承受和消逝的法则,我与稻田 达成默契。谁的孤独都微不足道, 不会比垄上一丛稻茬更高。 走吧,从这片田野里起身,这里不会丢失 一颗谷粒,曾被我分开的光和空气 也会像暗伤一样愈合。 小雪 多么单薄的一点小雪,还不够 覆盖穷人的屋顶 我爱它们触地死亡之前 在飘舞和融化中,尽情地完成自己 当生活已不能降下一场鹅毛大雪 我仍为那些意外的小欢喜 而感激,那些微细的,还未落地 就可能消融的,雪花一样意外的小欢喜 一壶水的沸腾,或冷却 有时候,一场爱的发生 就像一壶水。 烧水的人将壶坐在火上,就走了。 壶在火上兀自烧着, 打破原本的冰度,慢慢变暖, 变热,直到 细小的水泡在壶里 左奔右突,找不到出口, 沸腾,将壶盖 顶起,仿佛就要 决堤而出。 突然,火灭了。 水退回壶中, 平息,收敛,冷却, 回归太初。 这一壶沸腾过的静水, 没有遇到过茶叶, 甚至没有被烧水的人 喝过一口——质变 发生在最深处。 淬火 风箱在呼吼, 掀动火苗的红绸,猎猎有声。 砧子上一块铁坯,红得好像已经变软。 沉重的大锤轮番起落, 像安上弹簧的跳跃, 每一个位置都不偏不倚, 每一次力度都恰到好处。 他们合力打一块生铁, 翻来覆去,锤扁,抡圆, 风暴卷起山冈, 闪电擦亮海面, 像完成一场默契的合唱。 火花飞溅,在空气里开成绚烂, 直到砧子上的铁坯,揉成他们想要的形状。 他们合力打一块生铁, 只为一缕白烟 从火炉奔赴水缸, 像灵魂的洗礼, 滋地一声,生命完成淬火—— 不是坠落,不是毁灭, 他们已打出真铁,永不变形。 天气冷得让人脆弱 画作完成,一幅不像自己的自画像 透过油彩朝你陌生地微笑着。 像不像又有什么要紧, 最难看清的,或许就是自己。 天气冷得让人脆弱, 空气里混合着松节油和晚饭后余留的气味。 人坐在台灯下,有些恍然, 手,不自觉地就往灯罩上捂。 “再冷不烤灯盏火”,想起外婆的告诫。 天气预报里说,一场寒流自北而下。 寒流,带来的是冷,而不是雪花。 雪,落在别处。 没有了雪的期待,怎能叫冬天? 一年中最冷的日子, 一个稍稍凌乱的夜晚。 回忆,像钉子在夜色里敲响,粗暴而固执。 那些曾伤害过你的岁月, 仿佛还打着白色绷带,没有走远…… 睡吧。 睡吧,愿一夜无梦。 人世寒凉,唯棉花真实而温暖。 多么好,明早,你还会从棉花中醒来。 疼 她在厨房水池边清理晚餐的鱼, 忽然走神, 想起他曾对她说 “即使最郁闷时,我也会给自己蒸条鱼”, 她曾被这句话里的豁达和孩子气逗笑。 但这条鱼的表情攫住了她—— 它大张着嘴,白眼珠朝上翻, 一种对于结局的生动的惊惧和心有不甘, 甚至那被切成几截的身体, 也仿佛神经质地抽动了一下。 ——像一股电流,那种疼痛 也瞬间击中了她。 炉火和雪花 我喜欢炉火旁我们轻柔而漫长的交谈 你说出的每个词语都带着温度 和弯曲的弧线 火光捕捉着你的脸 我清楚地记得你的表情 像是身陷梦中,或一种深沉的幻觉 冬天已经过去,雪花依然不期而至 仿佛为了完成一种未竟的确认: 在自我的融化中,有些东西得以显现 我不忍告诉你,我更早地明了命运的难处 在秩序和内心之间,无论摧毁或重建 都有无可指责的理由 现在,炉火的余温还足以烤熟一只红薯 香气里我们拨弄着火石,但并不是为了吃它 未打扰的时光 推开院门就是棉花田。 起初,棉桃是沉甸甸的青色, 不知什么时候,棉田里飘出了白云。 午后,烟囱准时升起炊烟。 穿府绸褂子的外婆从菜园转到灶屋, 有时她站上井台,压动水泵的长柄, 把水从清凉的地底抽上来。 石榴树下,外公推着刨子,细细刨一块木头, 或者用墨斗,在木板上弹出一条黑线------ 刨花轻轻落了一地。 而我站在篱笆下,为一朵打碗碗花纠结不休: 想摘,又怕被打破碗的花神诅咒。 那时候,空气很慢, 成长很慢, 外公外婆的衰老也慢。 我以为,小院里的光阴是睡着的, 永远不会被我们的忙碌打扰。 最好的安排 七月,加州的李子已经熟透。 红得发紫的小蜜罐,藏在枝叶间。 哥哥搬来长梯, 我捧着篮子在树下接果子。 最高处的果实是摘不到的, 熟透了,就会从枝头掉下来, 被虫子和土壤吃掉。 伸出院墙外的那些, 是留给过路的小松鼠的。 夜里,它们会把没吃完的果核, 在石阶上顽皮地排成一溜儿。 而那些汁水最饱满的果子呢, 那是鸟雀们的零食, 它们的眼神儿可真好! 每一颗啄一口,就呼啦啦飞走了。 剩下的那些—— 才是上帝分给我们的。 给阳台上三盆花浇水 海檬草顶一把头重脚轻的绿伞, 看起来有些孤独。 一阵风来,就可以吹透它。 那些叶子之所以没有飞起来,是因为 半埋在土里的球形种子牵扯了它—— 它全部的生机也由这牵扯而来。 只要把水浇进那大张着嘴的褐色硬壳, 喜讯就飞快地传到叶子,它们从颓废中 欣然起身,摇晃着,获得新的姿态。 而虎尾兰则矜持得多,叶片执拗 如虎尾,常年沉默着,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长久沉默之后,欲望已变得滞重, 它只是一寸寸地膨胀着, 直到花盆被蓬勃地占满。 另外一盆,准确地说,只是一只空盆, 一只装满泥土的空盆—— 从前这里生长过凤仙花还是星星草, 只有泥土记得。 但每次,我仍习惯给这只空盆里的泥土 浇水,听细小的水分子 唤醒土壤,像伸入黑暗的闪电, 撬松泥土板结的空寂。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ongbailaa.com/cblszhj/1224.html
- 上一篇文章: 用万通妇炎康片做无炎女人
- 下一篇文章: 请记住这些北美木材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