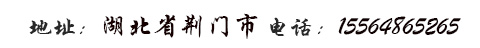金仁顺猿声小说月报12期预览
|
++++++++++精彩预览++++++++++ 他们傍晚时分到了南原府。天色阴沉,雨雾飘摇,远远看来,南原府仿佛一幅水墨图画,走进城内,方形木屋、蘑菇状土屋,错落拥挤,立于路边,木屋土屋之间,老树如亭,树干如一截静止的舞蹈,拧着腰身,华盖如伞,遮挡着细雨。 石板路时宽时窄,雨水似油,让轿夫们脚底板儿打滑,狭挤处有人从轿边经过,惹来轿夫们的叱骂。 “嚼草的驴马货,”有个脆生生的女声回敬,“龇牙咧嘴的,还想咬人不成?!” 崔梦阳撩起轿帘向外打量,一个女孩子娇黄短衣,袖口处嵌着红绿条纹,翻着白衬边,提着桃红长裙,从他轿边闪过,轿夫们的脏话乱蹄杂沓,追赶着她。女孩子不只声音,眉眼背影跟桔子亦有几分相似。 轿子在街道上又转过两个弯,停下来。轿夫们把轿子卸掉,叫的叫笑的笑骂的骂,有人唱起歌,有人随着歌声拧脖耸肩,舞动着臂膀。 崔梦阳从轿子里面出来,身体蜷太久了,粘叠在一起,花了一点儿时间才展扇似的打开。 玉姬也从轿子里面下来,紫色裙子外面加了件淡灰色马夹,侍女把一件紫葡萄色镶墨绿边的外氅展开,从她头顶上披下来。 宅邸是官府新近从一个盐商手里买来的,和南原府府尹大人书信中描述得差不多少,回字形,门外六级石阶,铺得整整齐齐,黑色木门对开,门环由黄铜打制,狮眼暴突,獠牙衔威。 房子新近粉刷过,在浓暮微雨中,白得像朵云彩,正待要飞涌起来,被上面翅膀状的黑屋顶压住了;屋檐角多铺了几叠瓦片,振翅欲飞,又似被下面的棉絮勾扯连缀住了。 崔梦阳打量着宅院,一时之间如坠梦里。 玉姬跟他说了句话,雨丝般被风扯凌乱了。 几个官差看见他们,叫了起来,一列官员随即从宅邸里鱼贯而出,官服齐整,态度恭敬,恭迎新任府使大人就任。几个仆从,都是白衣,灰扑扑几团烟雾似的,从宅邸里面悄无声息地奔出来,潦草见礼后,引领着轿夫和仆人们搬运行李,玉姬跟几位官员微微鞠躬,带着侍女进了宅邸。 崔梦阳跟官员们又回到客室,房间改变了不少,但框架还是旧时模样儿,仆人们端来新沏的热茶,崔梦阳跟官员们客套了几句。 “看大人着实面善,”府尹大人对崔梦阳说,“仿佛以前见过似的。” “府尹大人——”旁边有人接腔,“一向跟权贵人物都很面善的。” “不只权贵,”旁边的人打趣道,“花阁里的头牌,他也都面善的。” “确实如此,”府尹大人神色坦然,“待府使大人安顿下来,带大人考察南原府风俗人情的重任,舍我其谁。” 官员们笑起来。 他们离开后,崔梦阳独自沿着回廊,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儿,那棵老梨树还在,枝叶披拂,东面围墙的半月角门也是旧时模样儿,天色此时已经黑沉,侍女把角门边挂着的白纸灯笼点亮,门边有棵小树,灯光把树冠上面的一簇树叶照耀成青玉翡翠。 仆人请他去餐室。饭桌已经摆放停当,六个小菜依次排开,打糕粘着红豆豆泥,白切牛肉带着热气,旁边搁着碟辣椒酱,豆腐煎成金黄色,大酱汤在石锅里面沸滚着,带盖铜碗里面装着刚出锅的白米饭,玉姬的饭桌跟他相对摆在一起,饭桌的云头边框和狮爪桌脚,吸引了崔梦阳的视线。 “是宅邸里的器物,”玉姬说,“先将就用用。” “倘若夫人不中意这里——” “房子挺好,雅致洁净,还——”玉姬双手执壶,替他斟满酒杯,抬眼望着四周,“有些忧愁似的。” 她被自己的说法逗笑了。 崔梦阳把整杯酒倒进嘴里,一股热烫从喉咙冲进胃里,扭转翻腾矫若细龙,辛辣酒香昂头拧身重又蹿回喉咙里来,变成发自肺腑的咏叹,“咿——呀——” 崔梦阳的第一任岳丈权九,酒喝微醺,有时捏着筷子敲酒杯,有时拍着倒扣在盆里的瓢,“咿——呀——”拉长声调悠悠一叹之后,要么大江大河地唱个没完,要么耸肩晃膀提腿弯脚地跳起舞来。 十年前,崔梦阳在流花酒肆,除了身上的单衣,只余一张白面脸皮。他拿不准,投河和上吊,哪种死法更能彰显自己的贵族身份。 “小子,”隔着一桌酒客,权九冲他招手,“过来喝一杯。” 权九做夏布生意,进新货时,他喜欢把一整匹布抖落开来,搭在弯弯绕绕的支架上面。权九在阳光下面屈着身体,眯细了眼睛打量着布匹的纤维,抽动着鼻子,“我能闻到苎麻的味道。” 善媛在院子里摘花,侍女桔子跟在后面,隔着九弯十转的夏布,她仿佛行走在河流的对岸。 晚上吃饭的时候,崔梦阳看见屋角的白瓷罐子里面,插着一大蓬蓝色桔梗花,花苞宛若少女的帽子,鼓胀胀的,他的心里也鼓胀胀的,喝进肚里的酒,涓细绵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我年轻时种的苎麻,比竹子还直,破成麻线,”权九伸展双手,轻捻手指,“那麻线,比女人的头发还软,比伽倻琴琴弦还韧,上等的麻线才能织出上等的夏布——” 院子里有低笑声,伴随着裙裾轻拂木廊台的窸窸窣窣声。 崔梦阳的心变成了鼓槌,嘭嘭嘭地击打。他昏头涨脑了半天,才发现权九的注视。 “人在这里喝酒,”权九慢吞吞地说,“魂儿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 “失礼了!”他躬身拜了一拜。 权九沉吟片刻,张开手,一根一根数手指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晃你也住了不少日子了,”权九说,“明天吃蹄筋,喝告别酒,今晚好好歇着吧。” 崔梦阳坐在客房里,白色铺盖在月光下,仿佛一榻冰雪。权九在木廊台上又喝了半天,翻来覆去地哼唱:“江河水,江河水,白马万匹,碧龙一条;谁能抓住江河水?马蹄无影,龙爪无形,俱都落入江河水。” 崔梦阳的双腿跪坐得麻木肿胀,他从客房里出来,站在木廊台上,他的心跳声,掩盖了树梢上的微风和草丛里的虫鸣,跟权九的酒鼾声彼此唱和,成为这个夜晚的风雷雨暴。他走向后院,沿着“回”字,转弯,拉门拉开时悄无声息,桔子睡在厅房里面,一头长发散在枕头上,像个溺水的人;她的呼吸声急促,也像是性命攸关。 崔梦阳穿过房间,走过中间的梳洗室,他很奇怪自己,心都要跳出来了,仍旧闻得到胭脂和香粉的气息。 最后的四扇拉门,四幅屏风拦在他面前,春兰夏荷秋菊冬梅,风雅摇曳,又因了夜色幽暗,平添几分诡异。崔梦阳看着自己的手,月光下面灰白如死去,慢得仿佛不动,慢得好像拉门自己拉开了自己。 善媛坐起身来,丝被像堆雪滑落在她身前,她白色的睡衣上面,垂着发辫。宛若一笔浓墨。 崔梦阳跨步进去,在身后把门合上,走到榻前,双膝跪倒。 在淡淡的蓝灰色月光中,善媛面如宝镜,嘴唇薄嫩如花。 “我的性命属于小姐,”他甫一开口,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他们沉默良久。 善媛伸手触碰他的脸颊,指尖上沾了他的泪水,她放到了自己的舌尖上。 崔梦阳伏在她身上,把她压倒,衣衫下面摸到她的肋骨:原来,她的心是笼中鸟。 崔梦阳是被桔子叫醒的。他过了一会儿才搞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晨光从苔纸外面渗过来,毛茸茸的。家具物什,宛若浸在湖水里面。 “天塌地陷了,”小桔说,“亏您还睡得六神安稳。” 崔梦阳披上外衣,边系带子边奔出去,他跑得太急,拐过木廊台时,双脚像在冰面上一样,滑行了一段。 权九面对着院子里的梨树,入了迷似的,仿佛那棵梨树从天而降或者从地底下突然拔将出来,树上面结着樱桃大小的梨子,颗颗俱是神的启示,或者佛家般若。 善媛跪在权九脚边,那一瀑黑发,昨夜让崔梦阳雨雾雷电,几度迷失,现在云散雨收,在脑后绾成九龙戏珠样式的发髻,用一根发钗定住。 崔梦阳走到近前,看见她脸上泪痕尚湿。 “——是我的错。”崔梦阳傍着善媛跪下。 权九扭转过头来,他的目光像个大巴掌从头顶处压下来,让崔梦阳喘息艰难,权九沉默良久,双膝“轰隆”一声对着善媛跪下了,唬得善媛抬起头来,一时手足无措。 “是我的错!”权九的头“咚”的一声磕下去,“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地底下的母亲。” “父亲——”善媛眼泪迸送,伸手去扶权九。 权九甩脱了她,额角红肿,起身离去了,从那一刻起,他再也没正眼看过崔梦阳,再没跟他讲过一句话。他们在一个屋檐下又生活了几个月,权九早出晚归,夜里回来的时候,身上酒味儿能把蚊子醺醉,他在木廊台上唱《江河水》,唱得风嘶嘶雨潇潇,百转千回,时不时地中断,喝一口酒。 善媛坐起来,双臂抱紧双膝,头枕在膝盖上,听得泪珠盈眶。 崔梦阳拉她回被窝,被她挣脱开。善媛走到拉门边,跪着,匍匐于地,在暗夜中,像只不得家门而入的羔羊。 权九出事那天,夜深时才回到家,善媛让桔子用小石锅煮了辣牛尾汤,权九喝出一身大汗,大半夜的,在院子里洗澡。 “江河水,江河水——”他边用盆往身上泼水边唱,“白马万匹,碧龙一条——” “这位老人家是水草托生的吧?”崔梦阳嘟哝,“江河水江河水,灌了一天了还不让人睡觉?” 他们几乎是刚刚睡着,就被桔子吵醒了。 权九洗净了身体,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双手交叠放在胸前,神情安恬,头下的枕头浸透了血,乌沉沉变成了块老紫檀,血腥气压住了酒气,弥漫在清晨的空气中。 崔梦阳伸手摸了摸权九,他的手冰凉如瓷。他回头去看善媛,她的脸白蜡蜡的,神情恍惚,似在九霄云外。 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权九囤积的夏布卖掉。卖掉夏布之前,善媛像父亲一样,把夏布在阳光下面河水似的抖落开来。秋阳落在夏布上面,金斑点点,麻线纤维,脉络清晰。然后它们被卷起来,抽丝般,一匹匹被运出家门。 房间越来越空,崔梦阳带着满袋子的银子离开时,已经是初冬了。他离开前的那些日子,善媛泪眼汪汪,“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难过得不得了。” “人生最苦是别离。”崔梦阳心如刀绞,落下泪来。 善媛拿起崔梦阳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她的心像只兔子,蜷在胸腔里,惊恐不安,“你一走,好像天再也不会变亮了。” 每天至少有几十次,崔梦阳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跟善媛桔子,跟宅邸,跟夏布留在一起。让那些功名利禄见鬼去吧。 一直到他上车,探头出去,回头看着善媛和桔子站在大门口,身影轻飘飘,白细细的,而她们身后的宅院,巨大幽深,黑沉沉,空洞洞的。 他双手捂脸,放声痛哭。 崔梦阳回到阔别一年的汉城府,出入相熟的花阁,在软玉温香的时刻,他常会想起善媛,她的心被他带走了,像只小鸟,揣在他的心里,有时候会啄疼他,他从温暖香糯的身体旁边起身,穿衣离开花阁,外面空气清冽,新雪散发着淡淡的腥气,路白花花在脚前铺展,仿佛那一匹匹从宅邸里流出去的夏布。 那些夏布一路把他铺上了黄榜,取得了官职。虽然是七品微末,但以他的年纪阅历,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宗族家长召他去见面。父母死后,崔梦阳流连花阁,有次跟这位四品大人在一位当红舞伎的房间里狭路相逢,“真是失敬啊!”他被讥讽。 他两手相叠在身前,低下头。 “听说你卖了祖屋?” “只是暂赁出去,”他说,“我需要盘缠去投奔先父的朋友,他是个盐商,或可愿意资助我考取功名——” “盐商?资助你?他脑浆被盐水腌了?” “春风吹又生啊,”家长很客气,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身边,打量他,“果然是一表人才,难怪左相大人要招你当女婿呢。” 崔梦阳怔住了。 “以前你行差踏错,年少荒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家长说,“浪子回头,殊为难得。” “承蒙抬爱,我其实——” “且不说左相大人位高权重,难得他抬举你,听说那位玉姬小姐,”家长压低了声音,胡子刮到他脸上,狎昵地说道,“倾国倾城,体态风流,汉城府三千子弟,倒有两千九百九十九个为她辗转反侧呢。” “我住的那处宅邸,”在官府,崔梦阳问府尹大人,“之前是盐商自住吗?” “是啊,”府尹大人连忙问,“大人起居饮食有什么不适吗?” “那倒没有,”崔梦阳说,“我听仆从讲起,住过夏布商人——” “权九啊?”府尹大人笑了,“这个宅邸是他盖的,虽说不是贵族,但当年,权九是南原府数一数二的富人呢,只是后来——” 府尹大人突然截断话头儿,轻描淡写,“——陈年旧事,不提也罢。” 崔梦阳打开手里的折扇,搅动的风,掩饰了他的心跳。当年他随着权九出入过几次酒肆,初到南原府时,久闻这里是美女窠温柔乡,那时身上还有几两银子,他也曾在花阁里招揽过歌伎舞伎,不过他确实对这位府尹大人毫无印象。 左相大人替他争取到这个官缺时,无异于当头一棒,他让玉姬去跟父亲求情,只推说舍不得父母,不赴外任。但玉姬倒是兴致勃勃,“去南原府吃美食喝米酒听盘瑟俚,何乐而不为?听说还是个美人窝,我打赌大人嘴上说不想去,心里只怕五步并三步,急得跳脚呢。” 崔梦阳婚后入赘左相府,府邸里仆从如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有贵客来访时,左相大人经常招他作陪,与朝中重臣同席畅饮,指点江山,挥洒自如;回房间后,又有玉姬的花容月貌、轻言细语。 崔梦阳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从他决定成为左相大人女婿的那刻起,他就已经把南原府的人事,当成自己年少轻狂的一场大梦。他觉得没有什么好替善媛担心的:她年少美貌,守着一个大宅邸,多少市井少年巴不得跟她双宿双栖;或者她会被某个贵族包为外室,再或者,她因为相思过重,痴情而死—— 每次想到这里,崔梦阳都仿佛真的听到了噩耗,心如刀绞,泪流不止。 左相大人的女婿年少有为,聪明乖巧,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位上门女婿经常在睡梦中四处游荡,最后总会在书房里停留,写诗或者作画。 淫词艳句倒也罢了,仆人们不识字,但那些画可是一目了然,经常一夜间崔梦阳十几张二十几张连续画下来,宛若某场风流韵事的现场记录。仆人们每日清晨抢着去书房干活儿,有一次居然还打破了头。 “没有不透风的墙,您的那些画被传扬了出去,众说纷纭,”玉姬羞恼至极,“连累我都要被取笑打趣,真是丢人现眼。” “梦中鬼使神差,”崔梦阳申辩,“非我本心啊。” 找了郎中来看,崔梦阳并无实症;请了汉城府最有名的阴阳风水先生,他在府邸里四下巡查,最后,盯紧了崔梦阳,“只怕是有些阴债未偿。” “绝无此说。”崔梦阳瞥一眼左相大人,朗声作答,“梦阳少年时,两位高堂仙逝,倒是他们临去时对我颇觉愧欠。” 玉姬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忙碌过,花匠、泥水匠、木匠、画匠在府邸里进进出出,有天傍晚,崔梦阳从官府回到宅邸时,一个女孩子从门内闪出来,“公子回来了?” 崔梦阳晃花了眼,把女孩子当成桔子,他揉了下眼睛,发现确实是桔子站在眼前,跟他离开时相比,她现在是成年女子了。 “真的是公子回来了!”桔子从石阶上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跳下来,拉住他的衣襟,“小姐等您等得好苦啊。” 崔梦阳说不出话来。 “您不会把小姐忘到九霄云外了吧?”桔子见他没有反应,抓紧他的双臂,用力摇动,“当初您可是咬了手指写了血书、发了毒誓的——” “放肆!”崔梦阳身后的随从呵斥桔子。 桔子这才注意到他身上的官服,反身往宅邸里面跑,“小姐,小姐——” 崔梦阳睡梦里踏上几级石阶,进了大门,厅堂上的情景让他说不出话来:玉姬和善媛在木廊台上相对而坐,她们中间,隔着一个大大的绣架。桔子的一只鞋跑丢了,扔在木廊台前面。 玉姬瞪了桔子一眼,朝崔梦阳笑着施礼,“大人回来了?” 崔梦阳点点头,目光转向善媛,他们之间隔着一个庭院,几株石榴,千山万水。 十年不见,善媛变成了新识,乌发如鸦,眉目如画,淡灰色的衣裙绣着祥云。岁月并没有让她的美貌失色,反而打磨得更加光彩照人了。崔梦阳一如当年初见她时,口干舌燥,心如鹿撞。 “小姐——”桔子去拉善媛。 善媛回身看着桔子,直到她沉默,退到后面。 “这位就是府使大人。”玉姬给善媛介绍。 善媛看着崔梦阳,双手相叠,举过头顶,俯身大礼参拜。 “我让她们住下来了。”晚餐时,玉姬对崔梦阳说,“这位善媛小姐,虽说是个绣娘,举手投足,倒是个知情识趣的。桔子有些没轻没重,不过,跟仆人也计较不了那么多。” 汤匙滚烫,被崔梦阳整个塞进嘴里,他随即吐出来。 “没事儿吧?”玉姬问。 崔梦阳舌头火辣辣地焦痛,“——你从哪里找到她们的?” “我正想着要绣几个屏风,”玉姬说,“刚好桔子上门来卖绣品,你真该看看善媛绣的那些东西,花朵有香气,鸟儿能唱歌,她的绣针绣线都是魂灵附了体的。” …… ——摘自短篇小说《猿声》,作者金仁顺,原发《长江文艺》 阅读全文请购买《小说月报》年第12期,12月1日出刊 《小说月报》邮发代号6-38,每月1日出刊,年起每期定价10元,邮局订阅价8元;《小说月报》中篇小说专号邮发代号6-,每年4期,邮局订阅价15元。 《小说月报》在全国主要城市均有销售。订阅可咨询所在地邮局(所),网上订阅可至邮政报刊订阅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ongbailaa.com/cblycxz/6022.html
- 上一篇文章: 聚焦醴泉街道ldquo五化rd
- 下一篇文章: 彤程新材推出PBAT熔喷料,熔指高达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