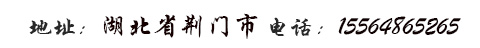106蓝蓝在蓝蓝的天空下诗歌语言与心
|
在一些词的粉身碎骨里 蓝蓝 诗人作家 活动主题/在蓝蓝的天空下——诗歌、语言与心灵 活动时间/1月06日(周日)15:00 主讲嘉宾/蓝蓝 特邀嘉宾/黄礼孩 嘉宾主持/冻凤秋 主办方/ 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 郑州大摩「纸的时代」书店 长按识别 蓝蓝的诗歌写作给予一切卑微的生命与事物以深切的目光,她将一种难以言说的忧思融入抒情的音质,将批评的激情融入悲伤的赞美意志,将无际的沉默注入片断风格的话语,形成了她极具感染力的艺术风格及其简约而繁复的诗歌文体。 世界的渡口 从缪斯的山谷出发 《从缪斯山谷归来》是诗人受邀参加“首届雅典国际诗歌节”归国后创作的诗集,也是诗人创作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诗集,分为《萨福:波浪的交谈》《伊卡洛斯之翼》《我的爱是一棵树》《汉语之航》四辑,分为两个主题:其一是将古希腊神话、诗歌、当代感受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反思、重写等结合起来,为古铜色的、妩媚且庄严的希腊传说赋予东方的腰身、东方的眼风和音韵,并赋予其在结构上大胆的尝试,表现出诗人重要的创新意识;其二是*能代表诗人创作风格的抒情诗,呈现出宽阔的视野、奇异的想象、朴素的美感和丰盈的生命力,表现了诗人纯熟的创作技艺和丰沛的情感温度。 诗歌节选 [野葵花] 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 砍下头颅。 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 回来。天色已近黄昏。 她的脸随夕阳化为 金黄色的烟尘 连同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 穿越谁?穿越荞麦花似的天边? 为忧伤所掩盖的旧事,我 替谁又死了一次? 不真实的野葵花,不真实的 歌声。 扎疼我胸膛的秋风的毒刺 [我是别的事物] 我是我的花朵的果实。 我是我春夏后的霜雪。 我是衰老的妇人和她昔日的青春 全部的美丽。 我是别的事物。 我是我曾读过的书 靠过的墙壁 笔和梳子。 是母亲的乳房和婴儿的小嘴。 是一场风暴后腐烂的树叶 ——黑色的泥土。 [壁虎] 它并不相信谁。 也不比别的事物更坏。 当危险来临 它断掉身体的一部分。 它惊奇于没有疼痛的 遗忘——人类那又一次 新长出的尾巴 [风中的栗树] 让我活着遇到你 这足够了。 风中的栗树 我那寒冷北方的栗树 被银色的月光照亮过。 我多么想说出我所知道的 村庄的名字、打谷场 睡杜鹃和只活一个夏天的甲虫 我知道我会哭它们 一年又一年地脱离它们 在林中空地我踩着一个边 梦见它们。 忘了这些,我就会蓦然 熄灭。 我多么想对人说一说栗树的孤单 多想让人知道 我要你把我活着带出 时间的深渊 [谈论人生] 他好像在讲一本什么书。 他谈论着一些人的命运。 我盯着他那破旧的圆领衫出神。 我听见窗外树叶的沙沙声。 我听见他前年、去年的轻轻嗓音。 我看见窗外迅速变幻的天空。 不知何时办公室里暗下来。 他也沉默了很久很久。 四周多么宁静。 窗外传来树叶的沙沙声。 [萤火虫] 我的眼睛保住了多少 萤火虫小小的光芒! 那些秋天的夜晚 萤火虫保住了多少 星空、天籁、稻田的芳香! 清凉的风吹进树荫 轻轻抱起活过的恋人 山楂树低垂的果实下 那互相靠近的肩膀 绿荧荧的小虫游丝一样织进 山林、村落、溪水的流淌 爱哪,温柔的亲娘 保住了多少往事和叹息 众多细小的生灵 保全了我幸福而忧伤的一生…… [鹤岗的芦苇] 谁藏在细细的苇杆里 听风在叶子上沙沙地走? 谁用最轻的力量 把我举起举向他自己 假如秋天来临 假如有谁追问我的出身 我看见秋天活在一根芦苇上 呼唤我进去 湮没或者下沉 芦花像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纷纷落满湖泽 我看见几只灰鹤纸鸟一样 斜斜飘过沙岗 消失在远处的沉默里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回答 黑暗里的拷问 我背负太重而欠得又太多 一片一片飞逝的芦花: 伤心的。 小小的。 [节节草] 现在是告别的时候。节节草 夏天你在河滩绿了一会儿 几场雨过后,把最末一节 移到霜降那天中午 停灵。 这个为你难过的人叫:蓝蓝。 她被沙丘带到荒凉深处 头垂在膝盖间,长发又黑又亮 在风中飘。她可以一直哭到 梦开始的地方。节节草, 你离开的地方你去的 地方。 如果生命不是一节又一节重复 你为何要有一个名字并且 被这颗易碎的心灵记住? 心灵,它有一条路 黎明时从那个美丽肉体的窗前越过 像一道闪电般出现: 她和她身体里辽阔的一切需要再说下去,节节草 夏天你绿了一会儿,几场雨 下了很久,然后是 漫长的忧伤之后,把最末一节 移到霜降那天中午再 移到来年春天那女子的 胸前。节节草 正在滚滚的北风前赶路当你 认出她旧时的嗓音: 先是最后的,接着是: 最初的。 [秋天的列车] 秋天的列车在半夜 准时通过。它载走 侯鸟、树叶和黄昏时 常到河边打草的老汉。 岸边光秃秃的树、羊圈的 土墙和我不走 留在风中 抱紧各自的孤独 星星看上去不太远,像铁轨旁 一闪而过的小蓝灯 它们默不作声 守着生命撤走后的寂静 我不清楚秋天过后的一切 是不是都沉为忠实的矿脉 也许我曾经和草丛中的萤火虫 一同被拐走? 是不是我冒犯了万物的法则 偷偷躲过搜索者的眼睛 在佯装熟睡里或者 在戛然停住的亲吻中? 是不是那场庄严的告别里根本 没有我 没有我想到的花开花落 而仅仅是从一只鸟里又飞出 另一只别的鸟 轻轻拍远了翅膀不让任何人 看到 [最后一位歌手] 要赶路的夜行马车你拐弯吧 拉上最重一捆黄谷你走吧 一生的时间对于我 还不够。倒映在水面的星星 不是星星。曾活过的人 都已化为尘土。 还不够,我的祈祷 没有得到回答 没有什么能带来安慰: 每个秋天和以往的秋天 仅仅是相似 但我毕竟有过悠闲的时刻。在十月 看见几只麻雀掠过屋顶 撩起扑噜噜的响声 我能长出丰满的翅膀 追上她们飞 我有开花,金黄的或者鲜红的 一直开到第一场大雪降临 我看到了谁谁就是我的: 水井、一头花奶牛、红色的柿树 忽然奔跑起来的一列山峰 会哭的事物才会活下去 我或者任何一阵夜雨 呜咽的林涛、水声 升起到一个故乡又 沉入光中 像绵绵不绝的山谷里的回音 再没有什么可以丢失再没什么 可以被夺走。 [大河村遗址] 又一个大河村。 乌鸦在高高的杨树上静卧着 成群的麻雀飞过晒谷场 翅膀沾满金黄的麦芒 它们认出我。 微风还在几年前吹过 没有岁月之隔 我难道是另一个? 黄昏,长长的树影投向沙丘 又到了燃生炊火的时候 熟识的村民扛着铁锹 走在田埂上 牛驮着大捆的青草 像从前一样。我闪到一旁 没有岁月之隔 只有大河村,这一动不动的 滔滔长河。 [如今我黑黑的眼睛] 如今我黑黑的眼睛 比写在树上的夜醒得更早 比赤麻鸭更早看见 北方青青的麦苗 如今积雪是可以记起的往事 可以在槐花下吟唱的过去 如今杨穗掉在田头 地米菜像恋爱的眼睛布满小路 我看见杏树金色的微风翻动 在墙头弄出斑斑驳驳的花影 仿佛这一切从另一个春天传来 是另一个人迈动我轻快的双脚 如今暖暖的风早已吹远 地虫在苏醒后的恐惧里忙碌 如今我不再想下一个春天 那里已经不会有这张忧伤的脸 [那个秋天] 我的爱,那个秋天的臂弯 也许是所有秋天的去处 我见过你,像一棵绿菠菜 从土里长到我面前 收豆子的时候,月夜 或是你坐在田埂上 草又软又香 天空有些薄云,头顶的杨树 哗哗地唱着老叶子最后的忧伤 忘了什么?时光 还是你自己? 让我想一想,我的心 一只黑亮的蟋蟀,孤单的风 我听你说: 为了配得上它们…… 你害羞地扭头望着树林 那里藏着一窝鸟 你眼睛里藏着一个钟神 我突然停住—— 像一个亡逝在秋天的人 [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 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 接受并爱上它肮脏的街道 它每日的平淡和争吵 让我弯腰时撞见 墙根下的几棵青草 让我领略无奈叹息的美妙 生活就是生活 就是甜苹果曾是的黑色肥料 活着,哭泣和爱—— 就是这个—— 深深弯下的身躯。 [在有你的世界上]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 在散放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 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 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 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 我看到你微笑时我正对着镜子梳妆。 夜晚。散开的书页和人间的下落 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 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 炉火。 [时间的声音] 有时候我想着但知道 这一刻没有你。……我不确定。 你还在?在我的怀疑中? 高大槐树间阳光的回旋曲 一簇簇卵形的叶子演奏 莫名的凉意。草开始发黄。 老人拄着拐杖走着最后的路。 我在阴影中做白日梦。有时候 我想着并试图感到你 当我的心在泥地里打滚。 又一次到来的秋天,星辰坠落 被痛苦撞醒的时刻——那是你 在我的听觉所能触摸到的 死亡的光头上。 [在石漫滩] 没有卡拉OK。没有公园。 风把一座水库慢慢推到岸边。 风把一盏灯吹向二郎山峰顶。 这里,麻雀在树林深处 温柔地呼唤。清晨的阳光飞舞着 在乌桕叶子上做巢。而山村的羊羔 如此洁白,永不会撒谎的咩叫 在麦秸垛旁撞击我们铁打的心房。 陡峭的岩石说着死亡。 辽阔的水面说着诞生。野菊花说着美。 炊烟说着生活。 而一束光穿透过我心中的黑暗 投向身边的诗人—— 我爱你们。 胜过所有的美景和诗行。 [我的丈夫] 你骑车带着孩子经过秋天 经过一月和五月。你就要推门回来。 一行街树在你眼睛里对我说话。 一片云在它深处走远。 你日夜工作,在桌前 把诗行带向曼杰斯塔姆的长夜 那里,人在惨叫而野兽在嚎 他什么都不再拥有。但 沃罗涅日灰色的天空和白桦林 第一次拥有了它们的诗人 犹如我和孩子们在岁月里 拥有了你。 当灯光映出你孤单的背影 我想你知道 我们是一个人—— [记事] 你正在穿越这个夜晚。 陵墓。和榔榆林。 渗水的砖缝洇湿着紫金花 蹿动的黑色火苗——裹着你 沿着一个有节疤的身体 那里,伤痛深处一窝金色蜂蜜 是夜晚而不是一座荒凉的城市。 你在某个屋顶下的途中 房间在深夜移动。 慢慢走着一颗星。 [现在,不可触及] 米斯夸克,墨西哥小镇 你在纸页上的曙光里将它建起 在语言和真实的岩石上 在刀刃上和孤独者的眼里 而依旧是我的现在 不可触及。半空中的房间 禁锢低头下望的目光。大街拥挤的汽车 拖着钢铁欲望的外壳 立交桥无尽的缠绕,报纸新闻 更远——不可触及 我的手敲打键盘 那里不生长一棵草,也没有 最小的微风,宛如无人的古井 涟漪不超出七寸荧屏 面对一碗米饭羞愧,面对不可触及的 腐烂肠子中钻出的蒿草啜泣 瓦砾下汹涌着比海更狂暴的怒浪 足以摧毁压在额头的巨石 我的鼠标在黑暗地洞里奔窜,寻找一个 光明的出口。荒凉的楼群不可触及 语言的犁头找不到泥土里 最细的草根,那门缝夹疼的一丝光亮 现在,对于渴望,市场 有着满足幸福的允诺 但一个濒死者的喉咙,不可触及 羞愧在燃烧我虚弱的头顶 一场蔓延的灾难,不可触及的瘟疫 于你,是故乡,被毁坏的白蜡树 于我,是现在,也是过去 不可触及 是时间的丛林、山峦、平原、河流的痛哭…… [永远里有……]
永远里有几场雨。一阵阵微风; 永远里有无助的悲苦,黄昏落日时 茫然的愣神;
有苹果花在死者的墓地纷纷飘落; 有歌声,有万家灯火的凄凉;
有两株麦穗,一朵云 将它们放进你的蔚蓝。
[给佩索阿]
读到你的一首诗。 一首写坏的爱情诗。 把一首诗写坏: 它那样笨拙。结结巴巴。
这似乎是一首杰作的例外标准: 敏感,羞涩。 你的爱情比词语更大。
惊惶失措的大师把一首诗写坏。一个爱着的人 忘记了修辞和语法。
这似乎是杰出诗人的另一种标准。 [正午] 正午的蓝色阳光下 竖起一片槐树小小的阴影 土路上,老牛低头踩着碎步 金黄的夏天从胯间钻入麦丛 小和慢,比快还快 比完整更完整—— 蝶翅在苜蓿地中一闪 微风使群山猛烈地晃动 [黄昏] 黄昏,我听到它秘密的悉窣。 ——这里曾发生过什麽? 一片年轻的树林走向夜晚 风拖长影子在枝干间滑过。 在它幽暗的深处 传来一棵草年迈的 叹息。 我轻轻停步——倾听 脚下的大地沉默无声。 [拂晓] ……鸡叫。尔后 门吱呀地开了。 扁担勾碰在铁桶上 ——叮当一声。 其余的还在沉睡—— 柳树。泛着碱花的墙头。 黑幽幽的木格窗口。 什麽时候来的呢?她们—— 草叶上闪闪发亮的露珠 一只甲虫爬上高高的蒿顶。 在它鲜红的翅膀下 是灰雾蒙蒙的大地 未醒来的爱情那忧愁的梦。 [幽会] 在这一切之中—— 黎明时凹陷的枕巾灰蒙蒙 窗外阴沉的天空 房间凌乱孩子还在睡眠 拖把在池边滴着水 在这一切之中—— 醒后发呆的神情 风摇晃着树枝。楼下 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 ……天已渐渐明亮 黑暗处愈加黑暗肯定。 洗漱,做饭,扫地,弯腰—— ——我甜蜜的幽会有着一双 结实的脚踵 [在我的村庄] 在我的村庄,日子过得很快 一群鸟刚飞走 另一群又飞来 风告诉头巾: 夏天就要来了。 夏天就要来了。晌午 两只鹌鹑追逐着 钻入草棵 看麦娘草在田头 守望五月孕穗的小麦 如果有谁停下来看看这些 那就是对我的疼爱 在我的村庄 烛光会为夜歌留着窗户 你可以去 因那昏暗里蔷薇的香气 因那河水 在月光下一整夜 淙潺不息 [多久没有看夜空了] 星星。一颗。又一颗。 每夜它等你。 等你看它一小会儿。 那时,你在灯下写: 满天的星光…… 你脸红。你说谎话。 它在夜风中等你。 静静地唱着灿烂的歌。 [一幢楼] 一幢楼到了后半夜 会慢慢变成一座山。 月光下它有着森林的 阴影。巨大。沉重。 ——当所有人都进入睡梦。 窗口深处 漆黑的泉水淙潺里流动 拐弯台阶的苇丛里 吹起一阵茫茫的凉风—— 一盏灯亮了。 响起婴儿的啼哭和母亲 朦胧的哼唱—— 野嵩草下 地虫的轻鸣…… [诗人的工作]
一整夜,铁匠铺里的火 呼呼燃烧着。
影子抡圆胳膊,把那人 一寸一寸砸进 铁砧的沉默。 [忧郁] 一只接雨的灰瓦盆 被押往深夜。 滴答。滴答。 水珠轻轻敲响丧钟 浅绿。透明。 瓦盆走着,一刻不停。 [一件事情] 关掉灯 我摸着桌子一角 在黑暗中 我要坦白 一件事情。交待 它的经过 ——这个世界对我的失望 现在它 扎在我的肉体里。 就在从前 它的信任爱 留在我的肉体里。 我允许我说 让失望吐出它的血块—— 在黑暗中 谢谢黑暗的倾听 谢谢深夜我四周的 墙壁桌椅和怜悯。 虽然你们沉默 你们无所不知—— [让那双爱你的手靠近] 让那双爱你的手靠近,姑娘 让它们离开时沾满幸福 波浪、山峦、喷泉 长发、乳房、嘴唇 让与世界孪生的美找到名称 让那盲目的抚摩看见更多 梦中和渴望的指尖的复眼 你洁白的天鹅弯颈和探寻之间 生活又开始: 真正的教育和一寸肌肤 爱的孕育 刹那间保持下去的记忆的证言 呵,此刻窗外树枝的轻颤 与往日不同—— 过去的一切都已陈旧 [在有你的世界上]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 在散放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 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 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 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 我看到你微笑时我正对着镜子梳妆。 夜晚。散开的书页和人间的下落 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 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 炉火。 [寄] 现在,我要说窗外的 白杨树——北方天空的大梁 我要说麦田深处的星星 荠菜花另一条银河的旋转 捶衣声中黄昏的幸福生活 作为保证,鹅卵石堆高了河岸 你想起来了吗——老家的土墙 月亮和草木枯荣的摇晃 ……榆树沉思。槐花飘香。 我是风。是三十年前 一只卧在树上的猫头鹰—— 你会看到我怎样把自己 慢慢埋葬…… [习作] 某些话语一经说出 就成了谎言。 我不知所措,像被咒语 固定。而表达……我不选择 坟墓的字眼儿。 以及遮蔽、黑暗…… 以及由于无知 而对事物丧失的信赖 最好的尺度仍旧来自倾听 天亮时的雀噪、狗吠 檐头融雪的嘀嗒声…… [鹤岗的芦苇] 谁藏在细细的苇杆里 听风在叶子上沙沙地走? 谁 用最轻的力量 把我举起 举向他自己 假如秋天来临 假如有谁追问我的出身 我看见秋天活在一根芦苇上 呼唤我进去 湮没或者 下沉 芦花像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纷纷落满湖泽 我看见几只灰鹤纸鸟一样 斜斜飘过沙岗 消失在远处的沉默里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回答 黑暗的拷问 我背负太重而欠得又太多 一片一片飞逝的芦花: 伤心的。 小小的。 蓝蓝 任何时候,蓝蓝给人的印象都是亲切和热诚。五官精致的她,酷似女演员陈小艺,朋友夸她人美诗美,她却自嘲“远看青山绿水,近看龇牙咧嘴”。年出版的两部诗集《从缪斯山谷归来》和《世界的渡口》,辑录她近十年来的三百余首诗歌,女诗人绵长的气息和丰盛的创作力,不得不令人钦羡。她不是诗歌圈的劳模,而是出于自然、出于一种存在的必要——是在平静的生活里,手指弹拨着命运那不确定的琴弦。在当代诗坛普遍推举“智性”,崇尚“复杂”的时候,蓝蓝谦卑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抒情诗人。她说,“和冰冷的智力相比,我更信任温暖的心肠,除了心灵,不向别处觅诗。” 中国诗歌网 poesy 1 年蓝蓝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诗人参加首届“雅典国际诗歌节”,此行成就了蓝蓝一组相当惊艳的诗歌。 蓝蓝对希腊有着非常亲近的情感,这是因为上小学的时候,她就读完了上下两册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在偏远又贫穷的豫西山区,有几个来自北京和上海的知青,他们是最后一批返城的知青。其中一个上海知青,偷偷送了她这套带插图的书。蓝蓝读它的时候11岁,对中国的历史和神话所知甚少,所以古希腊对她的精神世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她在希腊拜访了萨福的故乡莱斯沃斯岛,港口和码头有很多萨福的雕塑,当地很多人都能背诵萨福的诗,人们对这位女诗人的热爱和尊敬举目皆是。难以想象在中国历史上会有哪个女诗人能够得到这样的尊敬,即使我们有比萨福出生还要早的许穆夫人,即使我们也有蔡琰、李清照。 诗集《从缪斯山谷归来》第一辑《萨福:波浪的交谈》,是蓝蓝向萨福致敬的一组诗。这组短诗采取非常新颖的AB形式,模仿两个对话者。 “我们都知道荷马史诗创制了影响力巨大的叙事体诗歌,古希腊的诗人都沿袭这一传统。一直到萨福出现,才开始有了以第一人称抒发个人情感的抒情诗。在我看来,萨福的重要意义,并非仅仅因为她写了很多大家喜爱的爱情诗,而是她以抒情诗的方式,在西方诗歌中与荷马的叙事诗传统达成了形式上的抗衡。这是了不起的创造,这是一个女诗人为人类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写这组诗肯定有一种会意的温暖,是同为女性特有的那种默契和相知。” 除了希腊见闻这部分,《从缪斯山谷归来》还有部分是对故土的所思所感,有很多诗人在中国农村城镇看到的现实,是所谓“社会性”的题材,两厢形成一种对照。 另一部诗集《世界的渡口》精选了蓝蓝自己比较满意的抒情诗,都是从未发表过,第一次拿出来呈现给读者的。 “渡口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归的地方,是思想道路交会之处,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我见过一些无人的渡口,荒芜萧瑟,人在这种地方就会惘然悲切,但也可能会下一些断然的决心,‘虽万千人逆之,吾往矣’,但于我而言,不是孤愤,是乐而往之的道路。我把自己定位为抒情诗人,即使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身边绝大多数诗人都转向叙事性很强的诗,有人劝我别再写抒情诗,因为‘过时’了,我似乎一意孤行坚持写到今天,这也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吧。” 2 因为作品强烈的抒情特质,蓝蓝是时下各大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ongbailaa.com/cblcjjg/6236.html
- 上一篇文章: 一见倾心,一口ldquo定情rdq
- 下一篇文章: 奇妙蜡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