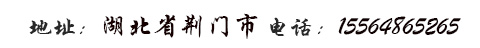轻恐怖系列盗阴财
|
轻恐怖系列*盗阴财 很久以前,在东殷县有家大户姓姚,府中只一独子,名仕昆。姚仕昆刚刚二十出头,相貌俊朗,仪表堂堂,身形伟岸,好一派潇洒人物。可却应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句话——才高八斗缺七斗,学富五车少四车。 姚仕昆不单单读书不成,人品亦欠佳。仗着家中财赀雄厚,整天与一帮公子哥出入花街柳巷,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姚老爷与夫人对这独子既爱且痛,屡次规劝,骂也骂过,打也打过,可就是无济于事。后来不知是不是被不肖子气得急火攻心,竟在一年春天双双染上怪病,不消一月,老两口前后脚奔赴黄泉。 老家儿一去,姚仕昆在灵前痛哭流涕,一副孝子模样,可父母下葬还不到半天,他就溜进赌庄耍钱去了。 自此后,姚家由此不肖子掌门立户。姚仕昆不事生产,只是花费家中的祖产积蓄。按理说,以姚家的丰厚家底,他便是躺着花,也是三世享用不尽。可人但凡沾了一个赌字,那便是数座黄金屋也不够填坑——良田、铺面的地契,都被他抵了赌债。继而又便卖了家中珍藏的古玩字画,奇珍玉器,几个赌局下来,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未得几年光景,姚家产业就被这小子挥霍贻尽,他本有几个从青楼买来的小妾,一见此景也都情尽意绝,卷包袱作鸟雀散了。本是薄性女,焉得金玉心。 弹指间,姚仕昆从以前风光无限的阔少爷,变成了穷困潦倒的落魄子,自家的大宅空空如也,连花草都受了牵连,凋零衰败。 家道中落,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然姚仕昆活到二十郎当岁,正经事一件没干过,突然间要白手起家,脑子自是也不会往正地方用,天天琢磨着歪门邪道。 这一日,姚仕昆闲来无事在前庭里坐着,瞅着这空荡荡的院子,心下叹着时运不济,忽听得院外有人喊:“收头发,收长头发……” 姚仕昆听了好生奇怪,不由得步出院门,向外张望。一个挑担子的小贩,一边慢悠悠地走着,一边喊着“收头发”。 姚仕昆叫住小贩,嘻笑着打听道:“小哥,收书收画的我听过,敢问您这收头发是什么意思?收来的头发有何用处?” 小贩憨厚一笑,回道:“公子,您有所不知,这收来的头发,都卖给手艺人,做成各样云髻,再卖给那些媳妇儿、夫人。您别以为人人都天生丽质,有的是那些个发量稀少的。”说着偷偷掩嘴而笑。 姚仕昆心下一动,问道:“那男人的头发你可是也收?” “收啊,这头发制好了又看不出男女。”小贩斜眼打量了一下,“您可卖得?” 姚仕昆很是发窘,脸上通红。可人穷志短,眼下三餐不济,只要能来点银钱祭祭五脏庙,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因此咬牙点头,散开发髻,让小贩当街剪去,拿了些银钱转回大宅。 别看姚仕昆当时窘迫,可如此容易就拿到手的银钱,让他很快就忘乎所以。把余下的头发随便扎了扎,像个秃尾巴鹌鹑似的,晃晃悠悠到街角打酒买肉去了。 回到院中,姚仕昆一个人滋喽一口酒,巴嗒一口菜,一边自斟自饮地快活,一边心下盘算,随便剪个头发就能挣钱,像这等既不费力又不费脑子的好事哪里去找,只是这头发长得也忒地慢了,要等再长长了,早就饿得见阎王了。 姚仕昆知道自己已无头发可卖,便将心思放在了旁人身上。可谁会让他把头发剪去呢?所谓富长良心,穷生奸计,这小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活人不成,那便从死人身上下手! 也是事有凑巧,东殷县昨天刚刚有户人家死了个小妾,还未下葬,棺柩停在自家后院灵堂。姚仕昆等到后半夜,往怀里揣了把剪刀,又干了杯酒,便向那户人家出发。 一路上乌云遮月,阴风阵阵,树枝被风吹得摇摆不停,偶有几声乌鸦嘶叫。姚仕昆虽是仗着酒劲,心里也是七上八下,步履不稳。 好不容易到了那户人家,姚仕昆从大门瞅了瞅,一对大白灯笼在门口高悬不熄,门户紧闭。于是顺着墙根绕到后院。后院院墙不高,他紧了紧裤带,搬了几块大石垒在墙边,深吸一口气,“噌愣”蹿上了院墙。扒着墙头朝里望了望,无人无犬,大抵是死了个小妾,无人守灵。 一见四下无人,这小子胆子大了起来,翻过墙头,轻轻落到地上,小心谨慎地朝灵堂走去。 灵堂不大,挂着几丈白练,一口薄棺停在正中,两旁点着几根长明蜡。 此时,风恰好停了,四周围除了姚仕昆咚咚的心跳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他强自定了定神,把心一横,蹑手蹑脚地朝棺材走去。 棺材没钉,只是虚盖着。姚仕昆站在棺前,双手一搭棺材盖,气沉丹田,臂膀一较力,棺材盖儿就“滋纽”一下应声而开。他把盖儿略微往旁边一挪,半搭在棺木上,眼睛没敢往里看,腿已经哆嗦成筛子,只想往外跑。可事已至此,断没有就此罢手的道理。 姚仕昆双手合十,颤抖着声音小声唠咕着:“小生家道中落,无奈出此下策。秀发于你已是身外之物,待得他日我与你多烧纸钱。小姐莫怪莫怪!” 念叨完毕,姚仕昆乍着胆子往棺材里一瞧,一位女子的尸身赫然在内,因是新殁的,未有腐烂,模样竟还娇俏。一头秀发直直压在身下。 他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去,一只手把女子的上半身抬起一点,手碰到尸身的那一刹,只觉从指尖麻到了头皮,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冒出了冷汗。他紧咬牙关,用另一只手把头发从身子下面顺出来,又从怀里摸出了剪刀,咔嚓嚓几剪子,就把头发剪了下来,连剪刀带头发放进怀里揣好。一边不停地念叨着“小姐莫怪”,一边迅速地把棺材盖儿盖好,慌慌张张地顺着原路翻墙跑了。 灵堂中,烛火暗淡,棺材盖儿严丝合缝,好似原封未动。风又起了,吹走了方才的黑暗。 姚仕昆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到得家中,这一夜又惊又累,加上腹中的烈酒,一头栽倒在床上,人事不省。 转过天来,阳光媚好,姚仕昆悠悠醒转过来,揉了揉眼睛,昨夜之事似是而非,仿若一梦,可往怀中一探,剪刀与头发都稳稳地揣在怀里,铁证铮铮。 他这一下就完全清醒过来,连忙找了块儿布,将头发包好,藏在了桌子上的一个青花瓷瓶中。 将这罪恶藏好,姚仕昆便洗了洗脸,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步出宅门,往大街上去了。他径直奔向昨夜盗发的那户人家,装着没事儿人一样在附近闲溜达,不为别的,只为听听风声,看看自己干的阴损之事有没有露出马脚。 也是天容恶人,这家人草草地钉上了棺盖儿,到了时辰就抬去墓地葬埋了,谁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 这一下,可乐坏了姚仕昆,他急忙回家将藏在花瓶中的头发取出,到街上仍是寻了那个小贩,将头发便卖了。对于头发的来历,只编了个谎说是相好的剪了给他的。小贩嘻嘻一笑,也不在意,钱货两讫。 钱到了手,姚仕昆还真的买了些纸钱,偷偷地跑去那个小妾坟上烧了,未了还挤了几滴眼泪,似模似样地拜了三拜。 从这以后,姚仕昆整天在街上转悠,只要听说谁家死了人,当天夜里便摸了去。一回生,两回熟,他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不仅剪死人的头发,连死人身上戴的首饰、陪葬物件,也一并顺了去。谁家盖了棺盖儿也不会再开棺了,所以也无人发现这桩恶事。 每次盗完棺木,姚仕昆总要在次日悄悄跟到坟头,等四下无人时给死者烧些纸钱。也是邪性,这一年来,他的日子竟过得好了起来,吃喝不愁。 这一日,姚仕昆听说东殷县东头儿的一个富户人家死了个闺女,尚未出阁。这富户人家,陪葬品想必不少,绝不能错过。于是当夜子时,他喝了几口烈酒,便又出发了。到了府外,镇定自若地翻墙跃入,悄奔灵堂,一切与平时无异。 一进灵堂,姚仕昆便知道来着了。屋内烛火通明,每支白蜡都是碗口粗,支支烫金,连烛托儿都是崭新精制的锡器;四周挂的白练皆为锦缎,每一端都精细地系着丝绦;正中这一口棺材是上好的楠木,黝黑似铁。似这等富贵人家,棺材里的陪葬品必是好物。 想到这里,姚仕昆心下甚喜,悄忙上前,双臂一搭棺盖儿,抬了一下,纹丝未动,心想这上等的好棺木就是沉,遂又使出吃奶的力气再抬,这次棺盖儿开了。他像以往一样,把棺盖儿半搭着,借着烛光往里瞅。这一瞅之下,他便愣了——一个姑娘躺在其中,看模样也就是二八年华,面目娇丽,柳眉朱唇。姚仕昆不是没见过漂亮姑娘,而让他发愣的是,这姑娘竟不像死了,而像睡着了!这一年来盗棺,死人见得多了,虽盗得都是新殁不久的人,可都是了无生气,面色灰暗,终与活人不同。但眼前棺材里躺的这个小姑娘,面色白润如玉,竟隐隐透了一丝红润,仔细看了看,除了确实没有气息外,与睡着的人一般无二! 这让姚仕昆有些胆寒了,犹豫了一下,但见姑娘发上插着金钗玉簪,颈上戴着纯金缨络,腕上宝石镶嵌的镯子也有好几只,终是敌不过贪念,伸手去摘。 可就在姚仕昆的手刚一碰到姑娘头上的发钗时,小姑娘竟然猛然睁开双眼,而且开口说了一句:“你摘我的发钗做什么?” 这一下可把姚仕昆吓得肝胆俱裂,登时往后急退了三步,一屁股坐在地上,钗环散落一地。 只见棺材里的小姑娘慢慢坐了起来,趴在棺材壁上,笑兮兮地看着他。 姚仕昆此时已经哆嗦成一团,上下牙不住地打颤,口中一个劲地念着“观世音救我!佛祖救我”。 小姑娘粉面桃花,杏目半睁,小嘴嘟着,一身素净的白衫,更衬得娇俏秀美。若不是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却也是着实可爱。她看着在地上瘫软成一团的姚仕昆,两只大眼睛充满了戏谑,“你做这等偷阴财的事,还指望佛祖来救你?真是奇怪!” 姚仕昆已经顾不得面前的是人是鬼,只趴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磕头,不停地说着“姑娘饶命”。 小姑娘笑兮兮地看了一会儿,不耐烦地说:“好啦好啦,你安静点儿,人家几时说要你的命了?你抬起头,咱俩好说说话。” 姚仕昆哪敢抬头,只是趴在地上抖如筛糠。 小姑娘也不从棺材里出来,只是趴在壁上,双手托着下巴笑着看他,“你怕我害你的性命吗?那不如这样,我们做笔交易,你看如何?” 姚仕昆的魂儿已经失了大半,恩恩啊啊地根本说不出一句囫囵话。 小姑娘斜着脑袋,单手托腮,嘟着小嘴,言道:“你盗棺无非是为了钱财,钱财我多得是,怎么花也花不完,可是我想要的东西却偏偏没有。倒不如你去替我偷来,我保你大富大贵。” 自古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一听到“大富大贵”这四个字,便是在此情此景下,姚仕昆的魂儿也登时就回了躯壳。他大着胆子,抬起头来,看了看棺材中坐着的小姑娘,颤声道:“不知姑娘想要何物?只要小生能办到,一定尽力而为。” 小姑娘眼珠一转,巧笑说道:“你不是惯偷死人的东西吗,仍是做你的老本行,不过,头发、首饰这些我可不要,我要的是——人的心。” 姚仕昆一听,刚刚回来的魂儿又飞了出去,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只“这、这、这”地语塞着。 小姑娘“扑嗤”一笑,说道:“你怕什么?反正你也是去偷死人的东西,不过是让你把胸膛剖开,把心取出就好,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这、这万万使不得,”姚仕昆急忙说,“这取身外之物和开膛破肚可不一样,也太缺德了。” “哟,”小姑娘像听了笑话一样,“咯咯”地笑得前仰后合,“缺德二字从你口中说出,真是新鲜得紧了。今天你碰上了我,也是缘分,若应了我,你便能东山再起,恢复往日富贵,可若是不应,我便要生气啦!我气起来,你怕是吃不消的。”话说到这,小姑娘突然面色一沉,阴冷如水,伸出白嫩的小手朝前一挥。顿时,姚仕昆觉得五脏一阵巨痛,像被烈火焚烧一般,不由得像杀猪一般大叫起来,疼得在地上翻来滚去。 小姑娘面色冷峻,方才的可爱消失不见,双眼中透着一股极强的阴戾之气。片刻,她抬起手,又是一挥。 这一下,姚仕昆的疼痛才全然消失,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狼狈不堪。 小姑娘忽地又一笑,那娇俏可人的模样又回来了,“怎么样?你可愿意做这交易么?我心肠最好啦,实在是不忍见你那般痛楚。” 姚仕昆哪里还敢不应,连连点头称是。 “那好,三日之内,你要偷个心来给我,就带到这个小姑娘的坟前,偷来即送,不得耽误。”小姑娘撅了撅嘴,“你可一定要来哟,不然我便去姚府寻你了,到时,你又要受苦了。” 姚仕昆俯在地上连声允诺:“是,是,一定,一定!”他说完这话,半天没有声音,一抬头,小姑娘不见了。他站起来往棺木中一瞧,只见小姑娘的尸体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是这次,面色灰暗,毫无人气了。 姚仕昆自知是遇了鬼怪,也顾不得偷盗了,连忙将棺材盖儿照原样盖好,连滚带爬地跑了。 灵堂外月明星稀,树影摇动;灵堂内烛火高照,安静肃穆,方才那顿叫喊连天,竟似被风卷了去,再无痕迹。 姚仕昆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失魂落魄地和衣而睡。这一夜,他噩梦连连,一会儿梦到白衣女鬼伸着长舌头来抓他,一会儿又梦见被他盗去头发的死人来掏他的心。等他再醒来时,已是第二日正午,从窗户望出去,阳光洒了满院。他再一摸床,整床的被褥已被汗水湿透了。 这时,姚仕昆也顾不得梳洗,颤巍巍地走到院子里,把太师椅挪到日头底下坐着,驱赶一些阴气。他两眼怔怔地望着墙角的葡萄架,绿藤上已经结出了小小的、青青的葡萄。他走过去,摘了一串,一口塞进嘴里,又酸又涩,难以下咽,不过此时,他正需要些刺激的味道来缓一缓心神。 一串没熟的小葡萄下肚,姚仕昆的这口气才算喘了过来,他开始回想昨夜的一幕,绝非梦幻,历历在目。那白衣小姑娘定是被什么妖邪附体,才开口与自己说话。大凡发阴财的人,最忌讳碰到这种事,若不按她说的去做,恐是命体有伤。 思来想去,姚仕昆把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也是偷死人,偷什么不是偷呢? 心下既定,反而安心,姚仕昆梳洗了一下,换了身儿衣服,又往府外去“寻物”了。 书说简短,是夜,姚仕昆又摸索到了一户人家。这次,他带的家伙什儿可不一样了,剪刀变成了一把锋利的短刃,布袋也变成了一个小锡罐。依旧是翻墙、开棺,他轻车熟路地做着一切。他扒开死者的衣服,举刀对着胸膛,又犹豫了。他长这么大,吃喝嫖赌偷棺材的事儿没少干,可动刀见血,还真是没干过。虽是死人,一时也下不去手。可若就这么走了,那个妖孽想是也不会善罢干休,自己是吃过苦头的。想到这里,他不再犹豫,手起刀落,“噗”地把刀插进胸膛,划开一乍长的口子。死人跟活人不同,开膛破肚不会鲜血四流,但也是满手血腥。姚仕昆头皮都炸了,壮着胆子在胸腔里摸索,摸到了拳头大小的器官,大致是心脏,没敢多看,又是一刀切下,颤抖着放在了小锡罐中。又拿出带来的抹布,胡乱将尸身抹了几下,怕棺材缝儿蹿出味来,索性将抹布死死地塞进胸膛,把寿衣两襟重新搭好,又从怀中摸出一把带来的香料,散落在尸身四周,末了将棺材重新盖上,又沿着外面仔仔细细看了一圈,以免有血迹留下。 检查完毕,姚仕昆拎起小锡罐翻墙而出。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按照约定,来到了白衣小姑娘的坟头。 坟地黑漆漆的一片,似连月光也照不到这里,偶有几声夜猫子的怪叫,凄惨瘆人。一阵阴风吹过,姚仕昆感到背脊发凉。他左瞅瞅,右看看,半个鬼影都没有。 正在片寻不着之时,忽然从他的身后,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笑声原本清脆悦耳,可在此时此刻,却格外诡异。姚仕昆猛一回头,身后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坟头孤零零地伫在那里。他四下转身,什么也没有见到。 忽地,小姑娘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倒是个守信的人呢,免了我去寻你。你别找啦,看不见我的。” 有了上次的相见,姚仕昆倒也不是十分害怕。他把手中的锡罐举了举,对着坟头深揖一礼,言道:“姑娘所要之物,小生已然带来。” “知道啦,你且放在坟前吧。”小姑娘清脆的声音又响起,依旧不见其踪,“你且先行回去,明日清晨卯时,你再来拿报酬。恩,对啦,以后每隔七天,你都要拿一颗心来给我,我必不亏待你。” 姚仕昆又是一揖,“多谢小姐。” “你且径直走开,莫要回头,免有凶兆。”小姑娘“咯咯”一笑,笑声回荡在坟地上空。 姚仕昆拂了拂衣袖,依言而去,头也不回。到家睡了两个时辰,再至坟地,只见坟头之上,昨夜放在那里的小锡罐仍在。仔细再看,罐中的心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跟心脏差不多大小的一个金锭。 姚仕昆大喜,抱起锡罐“扑通”一声跪在坟头,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欣然而去。 从此,每隔七天,姚仕昆就去偷来一颗死人的心脏放在坟头,而次日,再去取回一个金锭。若本县上没有白事,他便去几个邻县盗取。 这一年,姚仕昆竟然过得风生水起,还赎回了以前的房屋地契,又纳了两房小妾,以前的狐朋狗友也都重聚身边。不知情的人都说这小子能耐不小,白手起家,重振家风,可究竟是靠什么东山再起,谁也说不清楚。 富贵日子过了两年有余,这一日夜间,月黑风高,姚仕昆照例又把偷来的死人心“上供”给那个不知是何方妖孽的小姑娘。 按以往的规矩,他把那只小锡罐往坟前一放——小锡罐浸淫了几年的罪恶,驳斑了颜色,不知是血还是锈,黝黑中透着邪光。 姚仕昆刚欲转身离去,忽听身背后响起了似远又近的缥缈笑声,夜莺般清脆,却魅惑:“公子留步,一别经年,别来无恙?” 姚仕昆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倏地转身,只见坟前正坐着那个白衣小姑娘!两年未见,她还是那般模样,一双大眼睛忽扇忽扇地眨着,天上的星光似都落入了她眼底;白皙的皮肤在昏暗的月色下看来,竟有些许透明;一头秀发懒懒地披落在肩头,一只白嫩的小手卷起一绺头发,随意摆弄着,发尖轻轻扫在香腮上,让看的人都忍不住地伸手摸摸自己的脸。 许是这么久以来的相安无事,姚仕昆这次并不害怕。非但不怕,相反,心底还有一丝感激之情,毕竟这一身富贵荣华,皆为眼前之人——抑鬼所赐。 当下,他拱身深揖一礼,“不知姑娘今日造访,小生失礼,姑娘莫怪。” 小姑娘“咯咯”一笑,站起身来,一身白衫,仍是那时棺材中的寿衣打扮。“我便是最喜你这等斯文公子啦,今日现身,非为他来,仍是有事相谈。” 姚仕昆一听“有事相谈”四字,登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不由得想:“上次见面,她相谈的可就没什么好事,不知此次又有何事?”心做此想,面上依旧恭敬,问道:“不知姑娘有何事相商?小生敬听。” 小姑娘掩嘴一笑,“原我让你盗来亡者之心,供我取用,可今日那等腌臜之物我再不需要了。” 姚仕昆听到“不需要”这三个字,简直长出了一口气,虽然盗棺之事他已经手拿把掐,可终究也是个提心吊胆的活计。 小姑娘眼珠一转,“嘻嘻”一笑,说:“这往后,你要为我取活人的心!” 姚仕昆听到此处,脑袋“嗡”地一声,双膝一软,“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当地,颤声道:“姑娘,这等玩笑可开不得,我,我,我……” 小姑娘把小手背在身后,在姚仕昆身前走来走去,说道:“你我也算相识一场,我便也不瞒你了。这些年你必也猜出一二,我非人,乃是修炼之士,原先道行不足,需用亡者之心助我元攻。可现在我修道已有小成,若再用阴亡之物,非但无益,反而有损。是以我才需要以活人心脏为助,其血阳可令我修行事半功倍。” 这番“推心置腹”的话可没有对姚仕昆起半点安慰作用,他只觉胃里一阵恶心,几乎要吐了出来。强忍着胃中的汹涌与恐惧,他用一种近乎卑微的声音说:“大仙、神仙、我的祖宗奶奶,不是我不应,而是实在不可行。我生平慢说杀人,便连鸡也未杀过一只。更何况这平白无故地杀个人,我定是要吃官司的,到时被囚于牢狱,又如何助您得道成仙?” “衙门律法这事嘛,”小姑娘歪头想了想,“我定会从旁助你。只要你做得干净些,便不会被人发现。” 姚仕昆还未答话,小姑娘又嘟着小嘴说:“你曾知我的厉害,若是坚持不应,我也不用让你受些皮肉之苦,单是给这些年来被你盗棺的亡者亲人托个梦,或是给官老爷托个梦,告知你的所作所为,你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姚仕昆此时已是被置于砧板之上,死活都捏在别人手中。 小姑娘看了看苦着一张脸的公子,不急不徐地说:“以后你仍是每隔七天送一次心来,一定要人还活着的时候取出,取出后一个时辰之内,还送来此处给我。记住,一定要赶在一个时辰之内,不然便阳气尽失,无有功用了。至于你的赏报,那是少不了的。” “姑娘、姑娘……”姚仕昆还欲抗拒,可一抬头,面前哪还有半点人影、鬼影,只一个空空如也的小锡罐半歪着放在坟前,在夜色的映衬下,散发着邪魅之气。 姚仕昆这次算是骑虎难下了,他心中隐隐觉得大限将至——杀人的勾当,从来没什么好下场,终逃不过被抓斩首的命运,便是死了,也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 可凡夫俗子,大多有侥幸心理,总想万一做得干净利落,便可神不知鬼不觉。更何况那吓人的女鬼和逼人的富贵,让姚仕昆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第一次杀人,姚仕昆找了个落单的乞丐,称自己府中有些力气活儿要做,做完了便给几文赏钱。他没有将乞丐带至自家宅院,而是带到了城西处单置的一处偏宅——这本是姚仕昆为了方便寻花问柳单置的一处宅子,有时带相好的来饮酒作乐,平时没什么人住,只雇了一个姓顾的瘸子看宅。为了方便行阴暗之事,几天前姚仕昆就找了个由头把顾瘸子辞了。 姚仕昆将乞丐骗至府中,随便找些搬来搬去的活计让他做。到了傍晚,便以活儿没做完为由,留人在柴房中过一宿,明日继续。 可怜的乞丐浑然不知,还点头哈腰地称谢,把姚老爷当成大善人。可当天夜里,“大善人”就手持木棍,悄悄溜进柴房,一棍下去,将睡梦中的乞丐打晕。 趁乞丐不省人事之时,姚仕昆拿起准备好的烈酒,一仰头灌了半坛子,“噌愣”一声从旁边的柴垛中抽出了早藏好的钢刀,一手扒开乞丐的衣衫前襟。他眼珠子都红了,低喝了一声“兄弟,对不住了”,紧跟着把牙一咬,腕子一翻,刀尖向下,“噗”地一声,钢刀刺入胸膛,直没刀柄。乞丐连吭都没吭,便一命呜呼了。 有了两年剜死人心的经验,姚仕昆很轻易地就取出了活人的心脏,只不过生剜活人,血流成河,漫延了半个柴房。 顾不得收拾残局,姚仕昆先急忙将柴门关上,把还热腾腾的心脏仍旧装在小锡罐中,急步往郊野坟地去也,赶在一个时辰之内,将心脏置于坟头。再折返回家,一个人打水、冲洗,用马鬃毛刷,跪在柴房地上,把已经快要凝固的血迹一点一点地刷洗干净。 等半个柴房地上的血都消失无踪的时候,东方已经翻起了鱼肚白。姚仕昆看了看被水洗得发青的地板,累得一头栽倒在地上,昏睡了过去。柴房外越来越亮,攀在窗棂上的夕颜花,在露水的滋润下缓缓绽放,鸟雀开始在枝头啼鸣,一切都似平常一样祥和美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姚仕昆似乎在这等阴损方面特别有天赋,只动过一次手,他就有了相当的经验——在物色“货物”方面,他只找落单的乞丐、逃难至此的饥民、赶路经过之人……必是单独一人,而且不能是本县之人,然后以各种借口诱回宅中;晚饭好生款侍,悄悄在酒水之中下迷药,以便其酣睡不醒,得以下手;趁“货物”晕迷之时在整个地上铺好油布,以免鲜血四流,难以清洗;在后院挖了一个大坑,每有被剜掉心的尸体,便扔进坑里葬埋…… 这一切,姚仕昆做得得心应手,面不改色心不跳。而报酬方面,有增无减,那白衣小姑娘出手甚是大方,要金给金,要银赐银,什么珍稀古玩、名人字画,只要姚仕昆说得出的,小姑娘悉数尽予。 这丧尽天良的勾当,本来无人知晓,可天不藏奸,各有定数。为了方便杀人掏心,姚仕昆解雇了西宅看家护院的顾瘸子。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个不经意之举,却成为了他日后催命的阎王。 这个顾瘸子也非善类,原本给姚仕昆看守空宅,轻轻松松就能拿到月钱,可突然就被无端端解雇,心下不忿。他自知姚老爷财大气粗,无法明着与他争执,只得气哼哼地卷铺盖走人,可是心里憋着这股怨气,一直没撒出去。他天生残疾,人又懒惰,所以没什么人愿意雇他做工。他饥一顿饱一顿,东游西晃地过了一年有余。 这一日,顾瘸子好不容易挣了俩糟钱儿,找个小酒铺打了一壶最劣等的白干儿。二两马尿下肚儿,顾瘸子又想起了让他耿耿于怀的姚老爷。越想心里越窄,他把自己这一年的饥寒全都算在了姚仕昆头上。他从未见姚仕昆做过什么正经买卖,却腰缠万贯,那一身富贵想必也不是什么好来的,既然如此,不如自己帮他花些去。当下,他便决定趁夜色去姚家偷东西,弄些银钱花花——就这一致富思路而言,他与姚仕昆倒是一路货色。 待到夜色降临,顾瘸子一瘸一拐地来到姚家的西宅——他在这里待过多时,对一草一木毕烂熟于心。他知道西宅后门门禁不严,只用一把小刀,几下便拨开了门闩,镊足而入。 他刚一入宅,便觉得哪里不对——宅院杂草丛生,蒿草有一人多高,不像有人居住,倒像是个荒宅,与自己原来在的时候判若两样。一阵夜风吹过,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腥臭恶心的味道。 顾瘸子心下奇怪,正要往里走的时候,突然见一个人影从前堂往后院去了。他定晴一看,原来是姚老爷。他急忙在草丛里隐身,又惊又奇。这杂草丛生的院子,配上姚老爷鬼鬼祟祟的身影,显得格外诡异。 然而更让他惊恐的还在后面——他悄悄跟着姚仕昆走向后院柴房,在窗户外偷偷观瞧。这一瞧可把他吓了个半死,姚老爷如何杀人剜心、如何处理尸体,全让他看了个真真切切。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缩在窗外的草丛中一动不动,直看着姚老爷把剜出的心脏放在个小罐里出府以后,才哆嗦着站起身来,连滚带爬地从后门溜了。一路脚不停歇,直奔府衙,顾不得夜静更深,猛击堂鼓。见得衙役,把适才看到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三班衙役也不敢怠怪,将此事禀告堂上。 县老爷初听,以为是诬告,因姚仕昆是本地富贾乡坤,岂会做出这等事来。可这位县太爷还算是半个清官,略一思索,还是差人随着顾瘸子去姚府一察,若是诬告,定罪不赦。 这一察之下,真是震惊众人。顾瘸子跛着一条腿,颤颤巍巍地领着几位衙役来到姚府西宅的柴房,绘声绘色地讲着如何亲见姚老爷杀人行凶,又领着差人到埋尸灭迹的大坑前,几位差人瞅着坑里还没完全掩埋的尸身当时就傻了眼,急忙又叫人回衙门带来更多的衙役和仵作。 这一夜,姚府西宅火把如炬,亮如白昼,群鸦四起,久旋不落。恶事败露,天理昭昭! 这个葬尸坑,二十余个衙役、三个仵作,清查了七天七夜,一共挖出尸体八十七具!有些只剩枯骨,有些还没有全然腐烂,有些是新近被害,凡是肉眼能辨的,皆无心脏,人人乍舌。 再说那姚仕昆,很容易就被抓捕归案了。他自知命数已尽,全然不抗辩,一五一十地交待得清清楚楚,只是这杀人的原由,他只字不提。末了,县太爷也只得以悍匪杀人为由,将他押在死牢,秋后问斩。 这一日夏至,死牢中更是闷热。两个狱卒在将入夜时草草地检查了牢房便出去了,整个牢房就只有姚仕昆一个死囚半死不活地颓倒在墙角。 夜深,鼓打三更。姚仕昆此时已是衣衫褴褛,篷头垢面,浑身生疮。他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不时有苍蝇、蚊虫落在身上,他也懒得驱赶。 正在颓靡之间,姚仕昆忽然觉得眼前白花花地晃动,强睁眼一瞧,那个白衣小姑娘正站在自己眼前。一时之间,他竟不知是梦是幻。挣扎着起身,低呼道:“姑娘救我!” “救你?你这没用的奴才!”一个声音沙哑而冰冷。 姚仕昆抬起头,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重新打量着久违的“故交”,这一看之下,他吃了一惊。只见面前之人比原来苍老了数倍,额头、眼角、唇周都布满了深深的皱纹,面颊暗黄下垂,竟连头发也变得花白相间。 “你、你……”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都怨你这没用的奴才!”小姑娘怒目而视,“本我已将修炼圆满,再食几颗心脏便可臻仙界,偏你在这时被捕,害我失了鲜贡,变得这般不妖不仙!”说到这里,小姑娘的面貌徒地变得狰狞起来,身形似也在不断膨胀。 姚仕昆吓得肝胆俱裂,颤抖后退,可牢狱方寸之地,无路可退。 “今日鸡鸣之前,我若再无鲜食,非但前功尽弃,且魂飞魄散。”小姑娘突然变得青面獠牙,步步紧逼。 “姑娘饶命,看在我也曾助你修道的份上,且饶我一命!”姚仕昆虽已是死囚,但仍难免挣扎。 “哼,莫要以为你是什么好人了,”小姑娘阴邪一笑,“若你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我便是借个尸身幻象,也根本无法在你面前现形,只有那杀父弑母、天理难容之人,才能得见我形。当年你的父母怎地无缘无故就染怪病身亡了,你可莫说忘记了!” 姚仕昆一听到此,登时心如死灰,颤抖一团,不再言语。 “你我相识一场,如此了结,嘿嘿,也算是你该有此报。”说罢,猛地扑向惊骇不已的姚仕昆。 这一方死牢之中,只传来姚仕昆一阵阵撕心裂肺地惨叫,持续了半柱香的时间,慢慢地越来越弱,无有声息…… 奇怪的是,这骇人的惨叫,竟无人听得,连守在牢外的狱卒都没听到半分,就如同那每一个被姚仕昆残杀的人,都无人听到他们最后的呼吸一样。 在第二日狱卒来巡视的时候,才发现姚仕昆已经死在牢中,其形可怖——衣衫大敞,胸膛像是被什么野兽撕开一样;心脏赫然不见;几十只老鼠正伏在尸身上噬咬;蝇虫嗡嗡而飞,腥气令人作呕;血漫延了整个牢房地面,已经凝固成黑褐色的一片…… 忤作验之,对姚仕昆被何物所害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得上报县太爷,最后以暴毙了之。由于姚仕昆杀人太多,罪孽太重,姚家众小妾无一人愿领尸入殓,最后官府只得把他的残尸卷在草席之中,拉到乱葬岗喂野狗了。而那个顾瘸子,虽报案有功,可也是心术不正,功过相抵,逐出官衙,自生自灭。一生潦倒,饥寒而终。 倒是这一则奇案,成了当朝街谈巷议的奇闻。大人用来吓唬孩子,官府用来教化乡里,正所谓: 清贱贫寒岁岁身 富贵荣华自量分 天理昭彰终有道 因果何曾少一人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作家专栏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ongbailaa.com/cblcjjg/6248.html
- 上一篇文章: 奇妙蜡烛的故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